本帖最后由 万里 于 2016-11-21 20:14 编辑
一家子骨肉
太阳很好,娘坐在门前晒太阳,却满脸愁容。
爷爷前天晚上去了,停在大伯家。大伯家在村东头,我家在村西头。坐在门前,娘能清楚地看到大伯家门前来来往往吊唁的人,隐隐还能听到阵阵哭声。
娘也应该守在灵前的,可是娘不能去。娘清楚地记得二爷爷对她说过:你不能去跟她吵,就安心在自己家里待着,没人怪你。是好是歹,出殡后再说。你去了,要是闹开了,我唯你是问。你要不去,她敢闹到你家里,不用你动手我先灭了她。娘说,这种场合我不在,不得一辈子让人戳脊梁骨?二爷爷说,都是亲朋旧友,谁是谁非,心里都有一杆称,没人会说你。娘就不说话了,尽管满肚子委屈。
二爷爷是爷爷唯一的亲弟弟。二爷爷嘴里的她,是我的小婶子,一个典型的农村泼妇。爷爷临终前,大伯大娘和我爹我娘都在,唯独小叔小婶不在。他们住在镇上,平时几乎不回来看爷爷一眼。爷爷活着最后留下的一句话就是:我死了,就你们送我上山吧,就当少生了一个儿子!
爷爷是得胃癌走的。没病之前,一直跟着小叔过。小叔在镇上开了个批发部,爷爷帮着他照看孩子,兼顾生意,没早没晚地干。病倒了,小叔小婶说生意忙,没法伺候,一脚把爷爷踢回了乡下老家,爷爷差点当场气死。大娘是锯嘴的葫芦,平时连句话都说不周全,娘却气不过,一个人跑到镇上找小叔小婶理论,直说得小叔脸冒虚汗青筋暴跳。可是小婶拒不松口,在地上又是打滚,又是撒泼,没等娘动手,先啪啪打自己脸,然后骂娘丧心病狂,见她日子过得好,气不过了,来找她家的事。再接着服毒抹脖上吊全套用上,反要拿娘抵命。围观的人左三层右三层,指指点点看笑话。娘扭头看看一旁的小叔问:你当真不管?小叔不吭声。娘叹口气说:算了,就当没你这房吧,没的吵闹起来不成个样子,叫人笑话!
从此后,爷爷就由我家和大伯家轮流照顾。
这事到此也就算划上了个句号,只是小婶从此和娘成了死对头。
爷爷的病前前后后拖了三年。三年里,小婶没来过乡下看望爷爷一眼,小叔倒是背着小婶回来看过两次。中间又有两次让人捎了点钱回来。娘有次跟我们说,你小叔也算是有点孝心的。可爷爷不认可。爷爷常说小叔是有了媳妇忘了爹娘,是丧了良心的孬种坯子!爷爷又说,他身上的棉袄已经十来年了,里面的棉花又冷又硬,穿在身上不像袄子,倒像是铁片子。跟他们说了好几年也没给他重新做一身。娘听了就劝爷爷别说了,说自己过两天就去给他做。又说儿子好不好都是自己生自己养的,睁一眼闭一眼的过去得了,别传得人尽皆知的,难听。过两天,娘真的就将一件新表新里新棉花的袄子披到了爷爷身上。爷爷离去时,穿的就是这一件。
爷爷去了的第一晚,大伯和爹守在边上,娘在村口为爷爷烧了衣裤,说是到了那边冷,得多穿点。我们孙子辈的,有的跪在灵前,有的低头垂泪。大娘在门前放了一个火盆,一把一把往里面塞纸钱,塞一把哭一声,我苦命的爹也,你这辈子没享着福尽为子女受苦了。再塞一把,再哭一声:我早亡的爹也,你去不多远,下人们给你送钱来了,穷家富路,你可别省着花,多带点钱上路吧!大娘哭得像是唱词,让人觉得好笑。可大娘是真哭,哭一声,那泪珠儿就滚滚地往下淌,滴到火盆里,嘶的一声,瞬间一股白烟。二爷爷叹了口气说,行了,都别哭了,我哥有你们这样的下人,值了!好歹惜护点身子,这两天还有的忙呢!可大娘止不住,直到我娘从村口回来,还呜呜咽咽地哭着。娘在边上坐了好大一会才说,大嫂,你别哭了,爹活着时候咱尽心了,就是对得起他了,他去了是解脱,不遭罪了。
爹跟大伯问二爷爷要不要通知镇上的小叔。二爷爷望着门外黑洞洞的夜,拿不定主意。又扭头看了看已经没了的爷。爷的面容好安祥,就跟睡着了一样。原本的一脸病容,此刻倒是白净得很,还似挂了一抹淡淡的笑容。最终二爷爷说,算了,还是别通知了吧,让他安安心心地上山吧。
可是第二天,娘偷偷找人捎信给镇上的小叔,说爷没了,回不回来让他自己考虑。按娘的意思,小叔总是爷爷的亲生儿子,生死大事都没人告诉他一声,就不单单是面子问题了,以后想起来必定是个遗憾。
我想,娘的原意可能是想让小叔自己一个人回来。可她做梦也没想到,先回来的是小婶。小叔上县城进货去了,捎信的人就告诉了小婶。于是小婶一路哭一路骂,倒不像个人,竟是一股龙卷风从镇上卷了回来。说她是哭,其实也不算是哭,只是一声声的干嚎,脸上全没有一丝悲意,更不要说是掉一个泪蛋子了。说她是骂,也不算骂,按字面意思来理解,倒更像是“自责”:我苦命的爹呀!你才回乡下多长时间呀,就让那些个丧天良的给害死了呀!你活着的时候我没能好好伺候你,你死了我要亲自把你背上山垫棺材底!及至到了村口,又一把将自己的外套上衣扯下扔掉,发了疯似的往大伯家跑,一径跑一径喊,喊我娘的名字,说我娘是刽子手,用毒药将爷爷毒死了,她要跟我娘拼命为爷爷报仇。气得我娘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
其实也不是我娘一个人气,所有的人都气得发抖。可谁都知道跟这样的人讲理纯属白废口舌。如果肉也算是一味毒药,那我娘倒真是给爷爷喂了不少。爷爷因为手术切去了四分之三的胃,从此饮食方面就不太好了,怕硬怕冷怕酸怕甜。可每次我娘给他做的面条,他都会吃得很香。有一次爷爷忍不住问娘:为啥你做的面条比你大嫂做的好吃呢?娘笑着说:我手艺好呗!其实我知道,娘每次都会选上好的精肉剁成细细的肉泥,然后熬成汤给爷爷下面,肉泥太细,吃了易消化,爷爷只吃出了味道却吃不到肉块,但娘不说。娘觉得自己做了就开心,没什么好说的。
娘不说,娘也不让我们说。我眼看着娘为爷爷做的种种,却说不出口。以前也没觉得有什么,可现在听小婶说娘用药将爷爷毒死了,心里就弊屈得不行,仿佛整个胸腔里有一盆火在燃烧,怒气冲天就快要将我点爆了,恨不能马上从家里冲出去,迎上她当着众人的面狠狠扇她两个耳光。但是理智告诉我,这种场合撕扯打闹是要不得的。爷爷才刚刚走,一家子骨肉就要窝里斗,足够十里八村的人茶余饭后笑话十年!不光我知道,在坐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爹站在一边呼呼出粗气,大伯大娘半是愤怒半是惶恐地看着二爷爷,不知如何收场。
耳听着小婶的声音越来越近了,二爷爷终于站起了身,用眼神示意大家都别说话,然后转身对我娘说了那么一段话:你不能去跟她吵,就安心在自己家里待着,没人怪你。是好是歹,出殡后再说。你去了,要是闹开了,我唯你是问。你要不去,她敢闹到你家里,不用你动手我先灭了她。
坐在门口向东望,娘看见了大姑被人半搀着进了大伯家,我娘又看见小姑一路哭着钻进了大伯家,我娘还看见我爹的三姑被人背着进了大伯家。我爹的三姑就是我的三姑奶,比二爷爷还小两岁,可因为脑血栓偏瘫,已经卧床三年了。她上一次来走亲戚,还是没病的时候。再接着,各方亲朋都陆陆续续地来了,一时间鞭炮声、哀嚎声震天响。娘先时还专注地看着,可看着看着就越发觉出了自己的委屈:这个时间她本也应该在那里的。不看了吧,不看了吧!娘终于站起身来,深深叹了口气,扭身进屋将门关上了。 娘已经两天没怎么吃东西了,几天来,家里事多人多,也没觉着饿,只是身子软软的,想吃却也吃不下。中午,娘熬了一碗稀饭,端起来一口没吃就又放下了。从堂屋走到里屋,从前门走到后门,反身又进院子里去转了两圈,心里乱糟糟的不知道该干什么好。想着那边不知忙成什么样子了,又不能去看一眼。最后一咬牙,进里屋躺下了。
才躺下没多久,就听有人敲门。娘一咕噜爬起来,打开门,只见门前一嘟噜几个女人,正是大姑小姑还有趴在二表叔背上的三姑奶。几只眼一色的红肿着,一见到娘,还没眨巴两下,那眼皮就像得到了号令似的开闸卸洪了。娘慌着将人往屋里让,大姑还没进门就一把抓住娘的手说:二嫂,让你受委屈了。这不,我们几个一起来给你赔不是了。三姑奶更是拍着二表叔的背长声叹气:家里怎么着就出了这么个扫把星。娘觉得心里一热,嘴里忙着说没事。又慌着倒茶,又问那边怎么样了。小姑坐在娘的床帮子上就哭,说小婶子嘴里没个把门的,净满嘴瞎扯,大伯和我爹差点都忍不住要躲起来了,大伙好说歹劝,说没个亲儿子在边上守着不成个体统,总算把他两个给留下了。又亏了二爷爷发了好大一通火,小婶才略有所收敛。
好歹再熬过明天一天吧,等把人送上山入了土,就不用搭理她了,只是委屈了你啊!大姑最后做了这么个总结!
这天夜里,娘睡得特别踏实。爹在天快亮的时候,回来敲门,才把娘惊醒了。爹说,阴阳先生说要早出殡,可能天一亮就要抬棺出门,让娘准备一下。娘知道爹的意思,是想让自己送爷爷最后一程。一来怕人笑话,二来也怕以后自己遗憾。娘想了想说,我看着办吧,到时候就远远地跟着送葬的,不跟她打招面。爹挠挠头说行,然后转身离开了。
爹走了娘就起床收拾了。可等到娘走到大伯家场地下的草垛旁时,爷爷的棺木已经抬出大门了。那是一副上好的实木棺材,将近九百斤,八个大汉抬着走,都摇摇摆摆跟半酒微酣似的。大姑小姑跪在边上一声高似一声地哭,可声音再高也高不过小婶,那嗓门似鬼哭胜狼嚎,一声声都是对我娘的指控:天杀的,害了人心虚当缩头乌龟了,亲公公走了都不敢冒个影了。我苦命的爹啊,你这一走我再也见不到了呀,我拼了这条命帮你抱了仇,然后就来地下服侍你老人家呀!送爷爷的人很多,大家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小婶劝说着。可劝的人越多,她嚎的越响。两手拍得棺材啪啪响,又扯着抬棺的人,说是爷爷冤仇未报不能上山。抬棺的人本就累得不行,此刻更是站立不稳。其中有一位是我远房堂叔,气得大声喝问:行了别在这里假嚎啦,你是真孝顺,一个村里没一个人不知道,行了吧?难为你三年不来一趟,还能找到家门,赶快让老人家入土为安吧!可任凭大家怎么说,小婶只是扯着不放。
远远的,我看到了娘的身影似乎在微微颤抖。我知道她一定是在咬牙忍着。这时我离小婶也就几步远,眼见着我就要起身冲上前去了,这时候我看到了站在一旁的二爷爷飞快地跑上前去,跟着一脚将小婶踹到了屋里。二爷爷狠狠地啐了她一口,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我哥也不稀罕多你这么个贤惠媳妇。再敢闹一句,老子先灭了你!然后,就见二爷爷长出一口闷气,扭头说:大伙见笑了,对不住各位,让你们受累了!转过身来,二爷爷又向我娘站的地方招了招手喊我娘过来,早有人将孝衣递了过来。我娘接过去穿上,跟大姑小姑还有大娘说,咱们送爹上山!
正说着,远远看到村口一个身影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我眼尖,一眼就看到是小叔。不久,众人也都看清了。刚刚平息怒火的二爷爷瞬间又拉下了脸来,眼瞅着小叔奔到爷爷棺前双膝跪倒,二爷爷一记窝心脚就踹了过去。我娘到底离得最近,手又快,一惊之后连忙拉住二爷爷劝道:算了,他能来说明他心里还有这个亲老子。说到底,还是一家子骨肉呀!二爷爷愣住了,如一尊雕塑,半晌才缓缓放下脚来。
太阳缓缓升起了一角,挂在村头的树梢上,向大地挥洒着光明与温暖。在初升朝阳的照耀下,我娘仿佛是一尊身披霞衣的神佛,连瘫在屋里灰头土脸的小婶都看得呆住了,那一刻,恐惧羞愧之情隐隐浮现在她的脸上。只见二爷爷抬头望天说:我哥有福啊,这是个好天气!于是队伍重又前行。此刻,除了大姑小姑间或哭上一两声,大家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因为大家都知道,活着的时候尽心了,那么离去的时候就可以安心。最重要的是,活着的人依然能够好好地活下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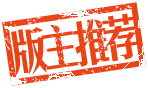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