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舅妈失踪几天了,已经四十岁的小表弟在电话里痛哭流涕。
年迈的妈妈和姨妈们哭着吵着要去找舅舅,说舅舅就不该守在那贵州的大山里,几十年了,不值得,说这次找到了坚决不让他再回去。
据说舅舅是被人陷害说他参加过国民党,被定为反革命才离家逃走的,走那年才19岁。几十年了,舅舅成了搁在妈妈和姨妈心口的一块石头。
我上初三那年舅舅是第一次回来,那时候外公外婆都过世了。舅舅穿着打了补丁的旧衣服,头上缠着脏得变了色的白帕子,黝黑的脸皱纹遍布胡子叭嚓,全身上下都那么分明地写着“落魄”,让妈妈和姨妈们都心痛不已。那次舅舅回来只住了几天就走了。妈妈她们虽然舍不得,但让她们宽慰的是,知道舅舅有一儿一女,那是她们弟弟的后人娘家的根。
第二次见到舅舅是在前几年,那时候舅舅已经在当坐堂医生,和我们同在一个城市。一二十年不见,舅舅皱纹深了白发多了。周围邻居都围到我家来,争着请舅舅替他们把脉开药方。
舅舅经常趁空闲的时候去大姨二姨和妈妈那里。遇上我们几家人婚嫁生辰,舅舅还会打电话让比我小一岁的表弟和表弟媳妇儿还有表妹一起回来热闹热闹,唯独舅娘从没来过,连提都没有人提起过。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二姨为什么舅舅从不带舅娘回来。一旁的表姐神秘地把我拉到一边:“你千万不要在妈妈他们几姊妹面前提舅娘的事儿,舅娘是别人的老婆。”一句话让我半天摸不着头脑。
后来,我还是断断续续从妈妈和姨妈那里知道了关于舅舅和舅娘的事。
据说舅舅逃到贵州的大山里后,一直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朝不保夕的生活,再怎么奋斗也不敢有家的奢想。为了躲避追捕,连用乱石砌成的窝也经常搬,从来不敢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
舅舅在大山深处的那些年月,生病从来不敢去看医生,都是自己采些草药治病。他从一位老苗医那里获得几本医书,加上自己苦心琢磨,又得到苗医指点,硬是学得了一套过硬的医术。大山里的村民们生病了,总是请舅舅去看,不但药到病除还节约了钱。
山里有一个妇女,丈夫瘫痪在床,膝下五个子女最大的十多岁,最小的几岁,日子过得艰苦异常。女人的丈夫需要长久的吃药,没有钱买药的女人就只有请舅舅去看,然后抓些草药。如此一来,虽然没能让瘫痪的男人站立起来,但是身体调养得还不错。看到这一家人生活的担子就压在一个女人身上,几个孩子又小,一家人就全靠着女人耕种的那几块薄地。青黄不接的季节,一家人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那时候因为舅舅会看病了,又是壮劳动力,便经常趁着去给男人看病的时候帮女人做些农活。瘫痪的男人看在眼里,感激在心里。终于有一次,他提出让舅舅以后就住在他家里,说有个固定的窝怎么也比东逃西躲的好。男人说,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这些年来,我的命靠的是你,我的家靠的也是你,所以我们绝不会出卖你!
从此舅舅有了一个“家”。十多年来,在瘫痪男人家的那一夜那是他睡得最安稳的一夜。
白天,舅舅干着一个大山农家男人所干的事;晚上,他挑灯夜读,深研中医理论。这么些年,作为一个大少爷的他早已习惯了大山深处清贫却宁静的生活。那些曾经的爱恨情仇,都随岁月沉淀成了他不愿翻开的泛黄记忆在心底封存。他只想好好钻研医术治病救人;好好替瘫痪男人顶起这个家,报答男人的收容之恩。
一天,舅舅在给瘫痪男人把脉的时候瘫痪男人突然问舅舅:“你都三四十岁的人了,就不想成个家吗?”
“像我这样东躲西藏的人,哪敢这种想法!”
“你现在不没有东躲西藏的了吗?就不想有个后?”男人顿了顿:“你是个好人,我看得出来。这个家交给你我放心,包括几个娃儿和……她……”
“……”舅舅一愣。这么多年一起劳作,他对这个女人不是没有想法。只是每每思想开小差,他都会痛恨自己怎么会像禽兽一样恩将仇报。
女人也是有着正常生理需求的一个人。这么多年,守着高位截瘫的丈夫,她对家里这个像丈夫一样顶着一个家的男人不是没有过一些情愫。很多时候,她都不敢直视这个和自己一起劳作的男人,怕一个不留意的眼神出卖了自己那颗有些荡漾的心。她也在心里骂过自己,怎么就那么水性杨花,自己男人还没死呢!
世界上有些看似铜墙铁壁一样的阻碍,其实捅破了就是一张纸。
本来瘫痪男人是要与女人离婚后再让女人和舅舅结婚的,怕去办证透露了舅舅的身份。考虑到这特殊情况,三个人商量着就不要在乎那一纸结婚证了。
一个晴天的傍晚,瘫痪男人把女人和舅舅叫到床前,牵着自己女人的手,亲手交给了舅舅。同时交给舅舅的,还有女人的后半辈子和一家人今后的日子。
就这样,瘫痪男人的女人成了我的舅娘。
听说小表弟出生那天徐然已经是深秋,却像夏天一样下起了倾盆大雨。他在刚刚脱离母体的时发出了一声嘹亮的啼哭后,再也没有那样无畏地发声过。他总是一个人低头不语,沉默得就像大山的山谷。
后来,小表妹又降生了。表弟表妹都是随瘫痪男人姓,叫瘫痪男人“爸爸”,叫舅舅“叔叔”。看着这一对儿女,瘫痪男人心里五味杂陈,但却当他们像宝贝一样,决不允许大的几个孩子欺负他们一丁点儿。
谁都能够推断出一个高位截瘫的男人是可能还播得了种的,连同小表弟一样大的孩子都知道表弟不是他瘫痪爸爸的儿子。尽管舅娘和瘫痪男人已经尽力让他们的五个孩子与小表弟和睦相处,但已经长大听够了人们冷嘲热讽的几个孩子还是把舅舅和小表弟小表妹拒于心门之外。
早就听说国家对舅舅这样的所谓反革命分子已经平反了。男人再次把三个人离婚结婚的事儿提了出来。但已经成家立业的男人的子女们坚决不同意,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反正,瘫痪男人早就是舅舅家的一份子,与那一纸结婚证离婚证没有半点儿关系。时间久了,那一纸结婚证也就发霉生锈了,唯留下一个关于柴米油盐的故事在烟火红尘里把血脉亲情紧紧相连。
前几年,小表妹也已经出嫁了。舅舅带着早已结婚生子的小表弟搬出了瘫痪男人的家,自己在相隔两座山的公路边修了楼房。小表弟继承了舅舅的衣钵开店行医,表弟媳妇儿开起了农家乐。逢年过节,一家人还是不忘带上礼物去看望孩子们早已成家立业不再身边的舅娘和瘫痪男人。当然,舅舅的家更是舅娘的家,只是舅娘放不下瘫痪在床的男人选择了坚守病床前,只有舅舅这边有什么大事或者舅舅每月回家去的时候舅娘才回到舅舅这边来。
这些年,出门打工挣了点儿钱的村民都把家搬出了大山,只有舅娘和那瘫痪男人的家还在那条深山沟里。原本舅舅劝说瘫痪男人过新屋这边来住的,这样舅娘照顾瘫痪男人也不用翻山越岭的两头跑。但是瘫痪男人的子女们不同意。就这样,瘫痪男人和小表弟的家相连的那条小路,被舅舅舅娘和表弟表妹的双脚磨得溜光。哪些地方下雨湿滑哪些地方有蛇出没,舅舅和舅娘更是清清楚楚。
在那条路上,舅舅舅妈没少摔倒过,没少被蛇咬过。如今,舅舅舅娘都年过七十,身体越来越不行了,但还是坚持走在那条只有他们已经人走的山路上。舅舅还配制了专门除蛇毒的药酒,两人走那条山路的时候就带在身上。
自从舅舅回重庆上班后,妈妈和姨妈们就经常念叨着,让已经有点儿小成就的表弟帮舅舅正儿八经的娶了舅娘过门,把瘫痪男人接过来好好在一起,也免得来来回回走那些陡峭的山路。
为这事儿,小表弟也回去和瘫痪男人一家商量过,惹得瘫痪男人的几个儿女不但和小表弟表妹大吵一架,还一两年都不来看瘫痪男人和舅娘一眼。看着瘫痪男人和舅妈伤心,舅舅心里也痛,表弟心里也跟着痛,就再也不敢提了。
因为瘫痪男人那里太偏僻也没牵电话线,手机更是没信号。所以小表弟见两天了舅舅都没回来才过去看。哪知道一过去,看到瘫痪男人滚在地上。说舅娘送舅舅走后,就一直没有回来过。小弟和表弟媳妇翻遍了那条山路都没找到人,这才打电话通知了表妹和妈妈几姊妹。
正当妈妈和姨妈们把我们小的辈召集起来要去找舅舅时,小表弟打来电话,说舅舅舅娘都已经找到了。“就在那条只有他们一家人走的山路的悬崖下。”小表弟说他现在还在医院。我们以为舅舅舅娘肯定是摔得不轻被送到医院了,但小表弟说:“我们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他们的手死死地握在一起,分都分不开。”
“那,医院……”
“我爸爸。听说我妈和叔叔走了,他一口气没喘得过来。”
正当小表弟还在和我们通话的时候,从小表弟的手机里传出医生的声音:“谁是病人家属?”
小表弟:“我是。”
“我们已经尽力了,请节哀!”
电话没有挂断,电话那头一片沉寂。良久,才传来表弟的抽泣:“姑姑,我是医生,但我却没能救回他们,为什么?为什么啊?”
冷风阵阵,夹杂着冷雨,似乎也夹杂着贵州大山深处淡淡的松针化泥的香味,在空中弥漫、飘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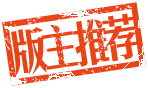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