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柳藏 于 2019-4-3 19:30 编辑
——读北岛散文集《青灯》
北岛的散文集《青灯》,薄薄148页。第二遍阅读耗时不多,思考的时间却比第一遍多得多。二次阅读,像是朋友久别重逢,光靠讲话交流是不够的。以笔记录观感,或许是一种补充。 《青灯》,词意沉郁,是孤独的象征。北岛的诗句”青灯掀开梦的一角/你顺手挽住火焰/化作漫天大雪”,别有一番豪壮,像是促织临冬鸣叫,悲情弥漫在短暂而局促的一生。青灯伴随流浪——“本是青灯不归人,却因浊酒留红尘”。灯影照壁,是心灵的囚禁,又像是修炼者的闭关入定。 在当代中国人的记忆中,北岛是中国诗歌王国里那杆标志性的蓝黑色旗帜。他最著名的诗作莫过于那首《回答》,“卑鄙通行证”和“高尚墓志铭”几乎成了滥殇。他的诗是生冷的铁锻造的长枪大戟,浑沉锐利,指向虚无的天空,引来无声的闪电——雷鸣在读者心中炸响。 诗人写散文或小说,具有独特的韵味。语句更为隽永,平淡之中灵光闪闪,诗意的小鱼儿在水底迎着阳光泛白。好的诗人不凑时趣,不屑于吟诵那些走马观花的流水帐,而是仰望天,俯看地,直面生死,剖开灵魂,将过去和将来拉近到面前。与神魔共舞,不畏强权。也因此,诗人的散文更有一种深邃的幽静,仿佛一条绵延了几百公里的暗河,冰冰凉凉,从一株桃树底下流出来。当然,也有一种阳刚澎湃的文字,一挨纸面,便如地底炽烈的熔岩,以无法抑制的激情,喷涌而出,半带自我毁灭式的冲击、吞噬,烤炙得人无法睁开眼睛。冷却后,坚硬漆黑,似乎地心深处抛出的真。 北岛的《青灯》属于后者;冰冷的坚硬,流动的线痕。此书共17篇文章,分成两辑,辑一是去国者的怀念,辑二是流浪诗人的世界。70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北岛成为中国现代朦胧诗的代表人物之一,经受了那个时代的特殊“关爱”。诚如日本作家永井荷风所言“艺术要至于和国家不相容时才高贵起来”——大凡文学一旦与政治挂勾,便充满了悲剧色彩。反叛者必然悲剧,归顺者一样是悲剧。这种悖论曾让沈从文无比痛苦:倘若每一个作者写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是各种附加效果。乐意这么做,他完了。他不乐意,也完了。北岛感慨“革命”与“权力”之间相互为敌,他成为他人眼中的“中国索尔仁尼琴”。 青灯伴随北岛流浪。“故国残月/重如石头”,照亮他的坚毅。“朝代盛衰/乌鸦即鼓声”,照出人世无常。《听风楼记》怀念冯亦代。那个不善言辞的翻译家冯伯伯,历尽人世沧桑,住在可“听人世间那凶险莫测的狂风”的小楼。十年动乱之后,记者采访问道:“你能简单地用几句话总结你的一生吗?”老人沉沉地说:“用不了几句话,用一个字就够了——难。”然后失态痛哭。《如果天空不死》中悼念熊秉明先生。这位雕塑家,也是诗人、书法家、学者、哲学家的通才,是中国传统文人和西方自由知识分子在最好意义上的结合,遗迹般的存在。北岛感恩熊先生在他父亲重病住院时,帮忙联系杨振宁先生出面,让他回到阔别13年之久的北京,见到了垂危的老父亲。诗人是尖刻的,他毫不留情的顺带讽刺了充斥今日的那些所谓专家们:“他们专业越分越细,路越走越窄,所掌握的知识纯粹用来混饭。在权力层面的延伸,从上到下,几乎个个懂行能干,但就是没有灵魂。”《远行》中悼念忘年交蔡其矫。这个中国当代文人中的异数,喜欢热闹,喜欢年轻美女,喜欢吃螃蟹。他是一辈子的不识时务:“在金钱万能的印尼,他离家出走;在革命走向胜利时,他弃官从文;在歌舞升平的时代,他书写民众疾苦;在禁欲主义的重围下,他以身试法;在万马齐喑的岁月,他高歌自由;在物质主义的昏梦中,他走遍大地……”在北岛的眼中,蔡其矫敢作敢为,是真男人,诗和远方的化身。与此相对,《与死亡干杯》记录刘羽,被时代无情蹂躏的文人。北岛为他含冤叫屈:“该挥霍青春年华时,他进了大狱;该干番事业时,他先撤了;该为时代推波助澜时,他忙着挣小钱;该安家过小日子时,他去国外打工;该退休享清福时,他把命都搭进去了。好像他的一生,只是为了证明这世道的荒谬。”北岛笔下有泪,长叹“这是个人与历史的误会,还是性格与命运的博弈?”文章末尾追忆1975年他们同游五台山的情景:“那时我们还年轻。穿过残垣断壁苍松古柏,我们来到山崖上。沐浴着夕阳,心静如水,我们向云雾飘荡的远方眺望。其实啥也看不到,生活的悲欢离合远在地平线以外。而眺望是一种青春的姿态。”诗一样的语句,穿越时空,读之令人不禁满怀怅然。岁月催人老,人无再青春。总有些诡异而重大的时刻,人于其中,仿佛蚁行万钧齿轮。凶多吉少。有的顷刻化成粉齑,有的劫后余生,自高空跌落,几十年后才听到自己坠地的响声。 《艾基在柏罗依特》也是悼亡式的文字,像是走在北岛前面的擎灯者。北岛借助他对忠诚于大地的至死不渝,折射“中国诗歌早就远离大地母亲,因无根而贫乏,无源而虚妄”。《我的日本朋友》和《芥末》是萍水相逢的故事。芥末曾为一名警官,像蚱蜢一样活得生鲜、充实。辑一的特例是《话说周氏兄弟》,山作和大荒这对来自南宁市武鸣县的两个壮族苦孩子,冲破层层雾障,一步步走向世界,兄弟俩济身身价昂贵的世界前十名在世画家,堪称美国式的奇迹。 辑二先是情感炽烈,篇章涉及智利政变、尼加拉瓜革命、前苏联解体、东西德嬗变等社会政治动荡,颇有跳出中国看中国的意味。大动荡的背景之下,哈罗德、聂鲁达等著名诗人,宛若飞溅的钢铁之花,瞬间耀眼,瞬间开谢。宁死不屈、饮弹自尽的阿连德总统,雏菊般的桑地诺之声戴茜,东德全体百姓沦为“贱民”的现状……人民的生活绝非幸福与否那么简单的说辞。岁月赋予北岛更宽广、更深远的思考。语句之中不乏颇具穿透力的见解,但是显然温和了许多,也多了更理性的思辨。他在柏林大屠杀纪念碑林中意识到,“俄国哲学家索洛维约认为有两种认识的方法,一种是外在的,即经验的和理性的,它面对的是现象的世界,获得是相对的知识;一种是内在的,它面向的是绝对的存在,与无条件的神秘的知识相联系”。由此推导出“与心灵无关的知识必导致精神的残缺,这恐怕也是我们深陷在现代化陷阱中的缘由之一”。北岛觉得“我们都是精神上的残疾人,不可救药”。我倒以为他应该再狠一点——没有灵魂的都是精神癌症患者。倘若如此,他便与《癌症楼》相契合了——事实上,北岛削瘦的脸型,尖下巴,低敛而冷峻的眼神,和索尔仁尼琴的确有几分相似。 《在中国这幅画的空白处》《多情的仙人掌》《旅行记》《三张唱片》《西风》五篇是带有体温的记叙。中国绘画原理中,留白是画面中最讲究的部分,让人回味。北岛自我定位“如果说中国是一幅画,那么香港就是这幅画中的留白,而我则是在这留白处无意洒落的一滴墨”。此番意境,是山岳看尽归去来的坦荡。作为一名作家,北岛没有辜负自己年轻时的内心召唤。他在《旅行记》中简要回顾自己的人生旅程。从长安街出发的男孩到航空港成为生活某种象征的常客,他始终处在“出发与到达之间,告别与重逢之间;在虚与实之间,生与死之间”。就像华碞,因世俗冷落,愤而流寓扬州,成为“扬州八怪”中的一杰。北岛的出走,“不仅仅是地理上,而是历史与意志、文化与反叛意义上的出走……在行走中失去了许多,失去的往往又成了财富。” 北岛和我父亲同龄,都是49年生人。《青灯》出版的时候,他们年届六十。弹指间,已是七十出头了。北岛说“一个人的行走范围就是他的世界”。我父亲的世界局囿于那个遥远的山村。我的世界比父亲大一点,但也被紧紧锁定在国内。蔡其矫的勇敢,芥末的敢于打拼,戴西的勇于践行理想,这些灵魂的力量,似乎已在我身上流失贻尽。北岛像夜间火车汽笛那孤独的声音,响彻夜空,而我则是快速掠过的影像微点。只是午夜梦回时,仍想“把酒临风/和中国一起老去”,期待“大门口的陌生人”,砸响门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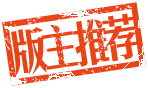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