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一孔 于 2019-6-3 09:28 编辑
文学是他的孽债 ——阅读标注之路遥和他的中长篇小说
路遥创造了一个游离于病句边缘的名句——早晨从中午开始。
这句话是一篇散文的名字,作者是路遥,是当时最为著名的小说家之一。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他的影响力依然很大,已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也许他不是最优秀的,但是他是最特别的,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像他那样对待写作,那是一个把文学当作生命并高于生命的人。在一本长篇小说的结尾,他用了较长的篇幅回顾了自己隐身于某个矿区创作的心路历程。他每天熬通宵,只有上午睡一会儿,也就是所谓的“早晨从中午开始”。那段时间,相伴他的只有山区的野风哀嚎的笼罩,还有以及永远不歇火的香烟和近乎充当兴奋剂作用的咖啡。他曾写道,他抽的香烟足可以绕地球几圈,而他的生活轨迹无非就是每天在树林里撒一泡黄黄的小便之外,便气喘吁吁地投入到他的鸿篇巨制当中,小说终于大功告成之后,他轰然倒下,只活了四十二岁。
他不是文学的精灵,而是文学的债主,最终以命相抵。
当然,我们可以说他有家族的肝病史,他好几个亲人都在盛年因肝病离去,也可以指责他既不科学的生活方式。写东西嘛!大可以像晏殊一样:一曲新词酒一杯!无心插柳,水到渠成,多好!犯不着较劲。可如果你再深入了解一下他这个人包括读读他的作品,你会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是一个天生具有使命感的人,陕西过于肥沃的文学土壤、贾平凹、陈忠实等已经名声在外使得他不甘心自己没有新的突破;家庭的贫寒和现实的苦难激发他必须要证明自己;天性当中的骄傲促使他不屑于平庸的创作。不写便罢,要写就得惊天动地。他给自己太高的定位,太大的野心,在传承了以柳青那一代人现实主义创作思想之后,他想发扬广大,挖得更深,走得更远,他想全息式地展示着他所生存的世界和这个世界里的芸芸众生。
他甚至想成为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
于是,在中篇小说《人生》因为电影的改编而爆红之后,他开始了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攀登。
曾经有人说,小说就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王朔说,基本上就是扯淡!当然是长篇小说更难写。据说有一次,路遥和贾平凹在文联开会结束上厕所的时候,路遥说咱俩谁尿得远,谁就写长篇。看来,路遥是使了很大的劲儿。巧合的是,贾平凹的确是在路遥逝世之后才写的长篇小说《废都》,之前都是中篇小说,比如《浮躁》《天狗》《白狼》等等。
可是,他写得并不轻松,如果要以现实主义为主旨的话,他必须准确地截取那个时代的横断面,而尚且年轻的他储备是远远不够的,只能全力以赴地做准备工作。他虽然熟悉他的村庄、他的学校,他的年轻时代,但这些只能保障他写出诸如《人生》那样的作品。那个故事的背景是他的周边,场景变换无非是家庭、学校和不大重要的广播站,人物的内心世界其实也并不复杂,不外乎现实的利益和质朴的爱情之间的纠结。他与其说是准确地触碰还不如说自己就感同身受到那一代人普遍的痛点,那就是高扬理想和爱情还是苟且于现实和生存?这和“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性质是一样的,再辅以醇厚的西北风信天游、黄土高原的苍凉厚重等等叠加在一起,引发全民共鸣并不在意料之外。
何况还有那一部万人空巷的同名电影?曾经,放映员们挑着放映机走到乡村,就在乡村的晒谷场上,黑压压的一群人——尤其是年轻人挤满了能够挤出来的所有空间,年轻的姑娘好奇地看着年轻高大的高加林,脸上一脸愤怒,却又不忍看到不太好的结局;卷起裤管的小伙子看到朴实美丽的刘巧珍心里悸动不已,以一种复杂的情绪着高加林的抛弃;至于像时尚靓丽的黄亚萍,似乎关联不大——那太高了,够不着,也就不去管她了。
那部电影几乎决定了那个时代的审美。高大帅气,浓眉大眼是男人的模板,大辫子,红脸蛋,可能还烫了几缕发是“女神”的标准。那时候如果说那个姑娘长得好看,人们会习惯地说:长得和刘巧珍一样,同样待遇的还有那个著名的林妹妹。事实上,不久后,扮演了刘巧珍的演员吴玉芳嫁给了当时最为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江嘉良,被认为是天生一对,多少就说明了人们的审美趣味。
但是,他将要写的《平凡的世界》囊括的东西太多了。时间跨度是好几十年,而这几十年又是中国当代变迁最为突出的几十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每个人都会因为时代的巨变而改变。人物大小上百,有在政治漩涡中心的高级领导,有迟钝地面对社会变化的基层干部,有新思潮冲击下各类年轻人的挣扎与上进,有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措手不及和逐渐适应,还有理想主义在物质主义抬头下的举步维艰和何去何从。此外,跟随着人物的变化,场地变迁也跨度很大,既有作者熟悉的农村,也有作者所不熟悉的城市和矿区,所谓移步换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很难的。
所以,如果我们不承认路遥是个天才的话——他当然不是,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他为这部小说所做的努力是超乎想象的。他既要努力梳理自己的生活和人物并转变为人物形象,更要尝试、探究他所不熟悉的一切未知,比如,他既然要安排孙少平成为一名矿工,他就应该了解矿工的生活是怎样的;他要想让田福军的形象更为立体,他就必须了解田福军的轨迹当中每一个步伐背后的各项政策和法律法规;他想写好已经是苏醒的中国大地,他就不能藏匿于自己的书房,而是要拼命吮吸泥土勃发的气息。
十年磨一剑,路遥磨得汗流浃背,却又欲罢不能。
他把自己所熟悉的东西写得游刃有余,他的乡村,他的农活,他的孙少安队长,他的田富贵书记都是活脱脱的。这些都是他的乡村记忆,他似乎只要把这些记忆转化为文字就可以了。而他着墨最多的也就是那个励志的青年小说第一主人公孙少平就有他一半的影子,他的思想动态甚至成长轨迹就是作者的直接呈现。路遥本身就是一个生活在底层极端贫穷但是始终艰难地扛着理想并试图杀出一条血路的年轻人,而他所有的武器和方向也只是可怜的文学,源动力也只有勤奋而已,他似乎可以稍稍骄傲的是文学毕竟没有完全愧疚他。写另一个还在路上的自己自然轻车熟路,这些都好理解。但是,对于那些他并不熟悉的领域,比如官场,比如生意场,比如矿区,他也并没有相形见绌,他曾反复地体验生活,他也曾搜集海量的报刊杂志信息。在一个大的要素拼盘面前,路遥实现了整体的有机链接,契合度比较高,保证了作品的完整。
不过,多年之后,我开始觉得所谓“术业有专攻”还是有些道理的。在那样篇幅的长篇小说面前,有些地方还是比较生硬的。回头想想王朔为什么说长篇小说难写,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内容多了,瑕疵自然很难遮掩完全,不写就没问题,写得太长,多少就会有些问题,《水浒》有这样的问题,否则金圣叹不会腰斩;《红楼梦》也是这样,只不过刚好后半截遇到了一个倒霉催儿的高鹗。
比如,田晓霞这个人物,这是一个理想化的完美女人,我几乎看到一半儿,就猜到这个故事没有结果。田晓霞是一个符号,一个作者给予了无限寄予的符号,他似乎觉得最好的女人只能垂怜于在他心目当中最为神圣的文学。可是作者觉得既然秉承现实主义的大旗,那么文学自觉告诉他,一个省委副书记的女儿是不可能和一个矿工走到一起的,哪怕那个矿工好像有那么点才华,还有那么点虚无缥缈的未来!而挑剔的作者是不会给她安排第三条出路的,他不甘心!于是,结果只能献身于他们的理想,在一场抢救当中被大水吞没——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是作者本人杀死了田晓霞。
那个年代张爱玲还没有畅销,我起初也不喜欢这个临水照花的女人,但读过白流苏尤其是曹七巧之后,才感觉到她的杀伤力。写女人,一般人还真不行,越把女人写得美轮美奂的人往往骨子里都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他们更擅长的是画出一个心目中的女人,增一分则肥,减一份则瘦。如果出现笔误,那就推倒重来。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把路遥和他的妻子的故事写成小说,可能更有冲击力,因为那才是理想与现实的真实再现,就是鲁迅的《伤逝》。
同样,孙少平似乎也很难有什么好的结果,错过了高考的那一代人更多的是被随后而来的年轻人迅速淘汰,混成了体制内的工人似乎已经相当幸运,再难走向更远。可作者不希望理想的死亡,奢望着文学的眷顾,于是一厢情愿地给他安排了文学的出路。不能否认,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成功的,但这些所谓成功的人物身上有着不可替代的特质,比如贾平凹的才气、陈忠实的坚守、莫言的批判,余华的深刻、他们已经悄悄地拓宽了视野,在继承的基础上开始颠覆,用前沿的文学特质填充并改变着各自固化的叙事,他们知道不仅仅需要在卧薪尝胆,还要死命地折腾,这些在孙少平身上一点点都没有展示,或许,那时候的孙少平和路遥一样认为文学可能只是一条线,最多是一个面,而没想到文学还应该是个房子,一片森林。
我有时候在想,如果路遥再多活几十年,会写出超出《平凡的世界》的作品吗?或许会,就像贾平凹,索性放开了写一本《废都》,不管成功与否,求新就变的步子是迈出来了。
好在东西是出来了。在我老家的小屋里,我买了两本路遥文选,一本是薄薄的《人生》和一些传播面不大广的中短篇小说、散文,一本是肿胀了一般的《平凡的世界》。我看他们的时候也只有二十来岁,奇怪的是已经不再为孙少平的励志抗争而惺惺相惜,也不再为田晓霞的完美而呼天抢地。我倒是觉得背后的那一个作者是个苦主,因为即便是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作者的用力之深,用情之深。
他就像一个还债的人,用一个自制的纤绳狠命地拉拽着自己,近乎疯癫一般地把自己憋在心里的所有一吐为快,然后释然、塌陷、毁灭。
路遥在某一次聊天的时候,用了最粗的一句话概述了自己与文学的宿命:狗日的文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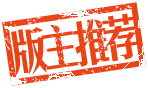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