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猪圈门前的空地上,大叔双手死死地抓住猪崽的四条腿,劁猪匠则用一只脚踩着猪崽的头。猪崽无助的尖叫声,让大叔惶恐不已。大叔觉得这次阉猪,怎么看都像极了三十年前自己被结扎时的场景。
劁猪匠从嘴里取下牙齿叼着的小刀,动作敏捷而精准地一划,用手一挤,两只殷红的睾丸飞了出来,滚落于地。
大叔突然感觉一阵剧烈的疼痛从裤裆里涌上来,双腿下意识地夹紧了下体。
二
一个多月没下雨了,地里的玉米被晒卷了叶子,蔫蔫的几乎没有了生气。这样的天气如果再持续几日,绝收就将成为不可逆转的定局。大婶抬头看了看火球一般肆意燃烧的太阳,觉得它的面目是那样的可憎。
我只不过是需要一场雨呀,哪怕是一场小雨也好!大婶大声哭喊着。
这样的哭喊,它这一生中只有两次。前一次是为了自己的两个女儿,她们在一场暴雨中葬身泥石流。
持续不断的烈日高温,再好的地也难以让庄家存活。何况,她的玉米地还算不上沃土。这就像她的身体,干涸欲裂。自从大叔动了手术后,夜里总是猛拍床沿哀叹提不上劲来。从此,大婶白天有事无事总往地里跑,直到天黑才怏怏回家。到了夜晚,她甚至害怕看见那张床,觉得它和死一般沉寂的墓地几乎没什么两样。她夜复一夜地洗衣、擦拭家具,直到很晚才合衣躺下睡个囫囵觉。
大婶一边抹泪,一边挥动锄头除草。明知此举已经没有意义,但她还是寄望于一场雨,能救活她的玉米。先铲除这些杂草,以免它们日后与自己的庄稼争夺水分。
二十年前那场撕心裂肺的大雨,现在却成了她日思夜想的奢望。
三
大叔将猪崽抱进猪圈。小猪崽如同遇上大赦,几步就蹿到角落里,瑟瑟发抖地回过头来,惊魂未定地看着大叔。那眼神里流露出来的,是极度的恐惧与无奈,以及难以言状的悲哀。
大叔家没有单独的客厅,厨房自然也就兼具了客厅的功能。
大叔陪着劁猪匠,抽烟喝茶聊着天,大婶则在灶台上忙着做饭。
大婶握着两只红里透白的猪睾丸,目光闪电般地扫了劁猪匠一下。劁猪匠顿时像遭遇蜂蜇似的,悚然一惊,香烟掉到了地上。
大婶将猪睾丸重重地拍在砧板上,两刀下去,将它们切成两半。再一刀刀下去,两只猪睾丸顷刻便成了面目全非的小肉片。
大叔闭上眼睛,上下牙随着大婶切猪睾丸的“哒哒”声不住地打架,烟吸得“咝咝”作响。
大婶盯着切成肉片的猪睾丸发呆,仿若看着自己血肉模糊的女儿。
饭菜上桌。大叔对炒猪睾丸视而不见,埋头大口大口地喝酒。劁猪匠的筷子刚伸到盛了炒猪睾丸的盘子里,被大婶不怒而威的目光逼得电击似地缩了回去。
送走了劁猪匠,大婶抬头看天上的太阳,多像一只硕大的睾丸啊,正以它的淫威,恣意地强暴着大地。
她突然在心里发问,老天爷为什么那么护短,咋就不把它也给阉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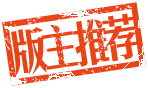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