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程
(1)
这天太阳好得不得了。明丽的太阳光从高大的梧桐树叶间斑驳地撒下来,将北京西路上一排排红漆脱落的旧窗户都照出一派勃勃生机。我看下时间,下午两点钟,再有两个小时我就要交班了。今天生意也够圆满。我坐在驾驶位上,把这张有些憔悴的脸迎着阳光,舒适地放松身体,眯上眼睛。
“你好,你有新的订单。”机器说。
本来不想再接单,但看下地址,就在北京西路上,我就按下了接单键。我停在一扇红漆脱落的旧窗户下,大声按喇叭,但没有人出来。我又打了电话,电话也没有人接听。我原本困倦,此刻又有点不耐烦,真想开车走路算了。我又抬头看看那扇红漆脱落的窗户,这扇旧窗户过去之后,是另一扇,另一扇过去之后,又是另一扇,无声的,苍老的,寂寂的。我叹了口气,下车,按照订单地址摁门铃。门里也是寂静的一片。就在我几乎颓然放弃的时候,门里面忽然响起了一个虚弱、苍老的声音:“请等一下。”我只好等在门外。外面的世界阳光已经明媚到极致,树叶接受了阳光的照射,枝枝叶叶都争先恐后散发出植物生命独具一格的蓬勃香气。门里是幽静的,神秘的,仿佛有什么气息丝丝缕缕透出来,气息仿佛也是香的,却是另一种沉淀的香气,在寂然里混着浓稠的哀婉。
(2)
门终于慢慢打开了。她拖着一个小小的行李箱慢慢走出来。她冲我微笑点点头,又欠身鞠躬。阳光照见她娇小的身躯和苍老的容颜。她头发不多,但丝丝银发在阳光的世界里,忽然具有了不可思议的光泽和风仪。她看上去大概有九十岁了,却仿佛不染一丝烟火尘埃气,显得既苍老又天真。她轻声对我说,“对不起啊,年轻人,让你久等了。”
我走上前一步帮她提箱子。她还没有关门,我不由向门内望了一眼。这是一间老公寓,屋内的座椅、沙发还有钢琴都盖上了白布。墙上光秃秃的,没有照片,没有画,没有时钟,没有任何装饰。但整面墙似乎都散发出一种活色生香的热量,神秘地宣告那些鲜艳存在过的生命痕迹。所有的家具都罩着白布,墙角边的一只纸箱也是。我盯着那纸箱,仿佛看见各种照片、挂件、饰品、纪念品正一桩桩一件件无声地破箱而出,飞到墙上,或安放在桌子上。我想我大概出现幻觉了。
“年轻人,可以麻烦你帮我把行李箱拿上车吗?”她轻声对我说。我如梦方醒,将她的行李箱放进后备箱,然后扶着她的手臂引她上车坐好。
“多谢你,年轻人。”
“不谢,您要去哪里?”
她慢慢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我,我看见上面写着的地址是“安化疗养院。”
(3)
安化疗养院是本市唯一一座临终委托医院。在这里收容的都是已宣告不治、踏入生命倒计时的老人或者病人——也许快节奏的都市生活的确让现代人忙碌也麻木了吧,连亲人的最后一程,干脆也委托给安化疗养院了。她这样独自拎着一个行李箱要搭我的车去安化疗养院,让我既心惊,又心酸。萍水相逢,我不便多问,也不知应对她说些什么?我只是默默关掉了计价器。我发动引擎,准备往安化疗养院开去。
“年轻人,可不可以麻烦你先载着我在这城市里转转?”她又轻声对我说。我说,“好。”这时候离开我交班差不多只有一个小时了。
“喔,这里的樱花还是这么漂亮……”
车驶在宣正街道。宣正街道的樱花正开得如同人间仙境一般迷人。我靠边停车,让她得以尽情欣赏。
“樱花最美,美在随风离枝。”她呢喃般轻语。我竟无言以对。
接下来,应她的要求,我车她去了莫北路。莫北路是颇有小资情怀的一条小街,街边开着各种衣饰和美食小店。我车得很慢。听见她轻声在数数,“一、二、三、四、五、六……”在第七棵梧桐树前,她轻轻说,“年轻人,烦你停一停。”第七棵梧桐树边现在是一个小小的鞋店。她说,“很久以前,我和我丈夫在这里开了一间小小面包店,我们做手工的面包和手工的酸奶,生意好好……”她叹一口气,又说,“那时候,我系着青花布的围裙,我的儿子和女儿就着面包和酸奶的香气,在后堂间做功课。”就像一个久远的梦,她轻易就迤逦地沉浸进去了。我默默地听着,觉得美,也觉得几分凄凉。几十年前。她的丈夫。她的儿子。她的女儿。几十年后。我不知时光的机器会利用这几样元素编织什么样的故事?此刻,她若感到开心,便是最好的。
车缓慢行驶在这城市中。明丽的阳光一点点往西去了。她的目的地是安化疗养院。在夕阳西坠之前,她忽然对我说,“年轻人,可不可以车回北京路去一次?”我早已和交班同事交涉了,请他多借给我两小时。我也不知为何要这样做。我想她也许要车回北京西路去拿点重要的东西。
(4)
返回北京西路,太阳正壮丽地下山。夕阳的余晖照耀着清雅的北京西路,照耀着北京西路上一排排散发着时光气质的老公寓,金光闪闪落在红漆脱落的老窗户上,是辉煌的回忆,缠绵的告别和诉不尽的伤心。
我扶着她下车。她颤巍巍站在自家门洞前,昂首看着自家的窗户。她面带笑意,平静地呼吸,深情地张望。那是一间空的公寓我已见到过了,但半生乃至一生的光辉岁月,她也许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吧?她具体的人生故事,我不知不晓,但我没来由,深深感动。我以为她要开门进去。但她默默站立了片刻,便对我说,“年轻人,耽误你太多时间,多谢你。现在烦你车我去安化疗养院吧。”
在开往安化疗养院的路上,我俩再未讲一句话。有些故事,不讲,比讲出来更动人,也许就是这种意境吧?
她下车的时候,将一串钥匙和一个牛皮信封交给我。她轻声说,“年轻人,多谢你今天下午对我的陪伴,我就不再付车钱给你了。”
我突然哽咽。因为我深知,我无法成全她。钥匙是她家的钥匙。那个牛皮信封里我猜是房产证之类的物品。我很清贫,但我也很感性。我不需要传奇,也不需要横财。我只需要安心和温暖。我想她也是。
“婆婆,我不能要,我要不起。”我把东西推过去。
她顶着满头银发优雅地站在那里,脸上露出了一丝疲倦。“那你只要我付车钱给你?可以……”她开始掏口袋。
“婆婆,不要。”车载她这一下午,难道只是这一趟车费的情缘吗?
我犹豫煎熬得厉害。我在想,我是不是该转身快快逃离?但我做不到。
“婆婆,你可否考虑,离开安化疗养院,我送你回北京西路……”我断断续续字斟句酌。
她看着我,皱纹横生的脸上慢慢绽开笑意,同时滚下大颗眼泪。
“婆婆,我不上班的时候,可以每天去北京西路照顾你,陪你……你想去哪里,我都车你去,好吗?”
夕阳渐渐收拢最后一丝余晖,黄昏隆重地登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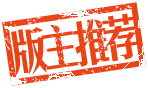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