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袁达清 于 2017-11-6 08:53 编辑
要是说我的父母有爱情,根据我的耳闻目睹,我是不肯相信的。但他们却在一起过了一辈子,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
听说,我的母亲当年是远近闻名的大美人,但家庭成分却是不好。外公、外婆出于某种考虑,将她嫁给了我的父亲——一个地地道道的贫下中农,且父母早已亡故,家里穷得连四壁都不全。我的父亲比母亲大了整整一轮,典型的大龄剩男,而且甚是木讷。
母亲出嫁那天,眼睛都哭肿了,本就单薄的身子,更加显得弱不禁风。她坐在父亲那四面漏风的破旧的“新房”里,以泪洗面。在父亲低声下气的哀求下,她总算吃了一个糖水鸡蛋。
睡觉的时候,父亲脱了外套就要上床。母亲一脚将父亲踹下床去,低声骂道,滚远点!
父亲从地上爬起来,尴尬地笑笑,抱起一床被子就要往外走。
母亲低声喝道,去哪里?
父亲回过头,木讷地笑着说,我去柴房睡。
母亲瞪着父亲,愠怒道,你是成心要让别人戳我脊梁骨么?
父亲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放下被子就要往床上爬。
母亲声音很小,但却极为严厉,喝道,我让你上床了吗?!
父亲挠着头,手脚无措,嗫嚅道,不能睡柴房,又不能睡床上,你让我睡哪里呀?
母亲狠狠地白了父亲一眼,指了指地上。
父亲轻轻叹了一口气,在床边的地上打了地铺。
母亲是不大和父亲说话的,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也往往是诸如“喂!水缸里没水了”之类的话。
父亲倒也不生气,乐呵呵地挑起水桶去挑水。
父母随着社员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就这样清汤寡水地过着。
母亲是“四类分子”的女儿,而且是百里挑一的 “四类分子”的漂亮的女儿,这让她极是显眼。当红卫兵来揪斗正在做午饭的母亲时,正好父亲割草回来了。父亲扔下挑在肩上的青草,抽出扁担,挥舞着朝那帮人疯了一般扑去。那群人大恐,只恨腿短,哭爹喊娘四散而逃。
大队工作组的组长也曾来给母亲改造过思想。他流着涎水,亲切地拉着母亲的手,激情而又不乏严肃地给母亲大谈漫漫人生和崇高理想。
砍柴回来的父亲见状大怒,抡起斧头,仅仅一斧,就将院子里的一棵小枣树拦腰砍断。
工作组组长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逃离。
人们很是诧异,一向老实巴交的父亲,怎么有时像只凶悍异常的老虎。诧异归诧异,没人再来找母亲的麻烦却是不争的事实。
母亲对待父亲的脸色好了些许,但也仅仅是好了些许而已。
一年过后,父亲和母亲明显感觉到周围人们眼神的异样,不时有人在身后指指点点。有几次,父亲隐约听到有人在说,究竟是地贫不长庄稼,还是农夫耕田不力?父亲摇摇头,微微苦笑。
性如烈火的外公和小脚外婆从二十里外心急火燎地赶来。面对外公的厉声指责和外婆婆娑的泪水,母亲捂着脸放声大哭。父亲蹲在墙角,吧嗒吧嗒地吸着旱烟,低着头,仿佛自己是罪犯一般。
又一年后,我出生了。父亲兴奋得如同孩子,抱着我朗声大笑,惊飞了屋顶上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
接下来,母亲一年一胎,陆续生下了四个妹妹。
母亲叹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气后,对父亲开始和颜悦色起来,跟他说话也多了。父亲兴奋得成天咧开嘴笑,干活更卖力了,仿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有一次,母亲对父亲说,没能给你生个儿子,我造孽哩!
父亲眯着眼笑,说,五朵金花,好看哩!你瞧瞧,她们长得多像你,讨人喜爱着哩!
多了五张吃饭的嘴,本就贫困的家庭,日子就更加拮据了。父亲除了在队里出工挣工分,农闲时还进山为林业站伐木,换取微薄的工钱贴补家用。
母亲吩咐我们姐妹到田里拾麦穗、稻穗,到地里去铲未挖尽的土豆、红薯。她也带我们上山采天门冬、羌活、何首乌,晒干后变卖了换些油盐。
母亲有一双点石为金的妙手,无论什么食物,哪怕是石磨磨出来的粗糙的玉米碴子,只要经过她的手做出饭来,吃起来就是比别家的香。吃饭的时候,父亲总是笑眯眯地对我们姐妹说,你们娘可是大户人家出身,手巧着哩!我们家有你们娘,是咱们爷儿几个前世修来的福哩!
母亲吃着饭,剜了父亲一眼,但她的眼角分明带着几分笑意。
春天虽然姗姗来迟,但毕竟来了。土地承包后,母亲那与生俱来的大户人家精于筹谋的脑子有了施展的天地。水田种稻子自是不说,旱地中,肥地种玉米,套种黄豆;薄地种高粱,间种土豆;怕涝的花生种在透气性好的沙地,籽粒饱满,产量高;透水性差的黄泥地,母亲用来种辣椒。母亲说,黄泥地种出来的辣椒,颜色好,辣度高,质量上乘。因地制宜才能有好收成,不能像牛一样蛮干,种庄稼也得用脑子。父亲频频点头,像一个小学生,围着母亲的指挥棒转。
父亲忙得成天在地里侍弄庄稼,身子晒得黝黑,人瘦了,但却精气神十足。
母亲每天午饭都会给父亲煎两个荷包蛋,并规定我们在父亲回家吃饭以前,把饭吃好了去上学。我们知道,母亲是怕疼爱我们的父亲将鸡蛋给我们吃。
夏收和秋收后,我家的粮食和经济作物都获得了大丰收。大年三十,父亲眯着眼算了半天,喜不自胜,家里比其他人家的收入多了不少。
你们娘是诸葛亮啊!父亲笑呵呵地对我们说。
两年后,我家盖了新瓦房,敞亮、气派,周围的人“啧啧”赞叹。
一个夏天的下午,我放学回家,看见一个衣着考究的男人,坐在堂屋里和母亲说话。在门口听见母亲叫他“生哥”。母亲叹着气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现在过得挺好,孩子们也好。孩子们的爹是个实诚人,好着哩!
我进屋去,那男人和善地看着我笑笑,站起身告辞,说,那就好,我也就放心了。说完用手巾擦了擦眼睛。
随母亲送客人出院子时,我分明看见父亲坐在旁边的竹林里,埋着头抽烟,不时举起衣袖擦眼睛。
我们姐妹一个个长大。我留在了父母身边,招了个孝顺的上门女婿。妹妹们上中专,考大学,工作,结婚,生子,一路顺风顺水。当然,我们知道,父母为我们操碎了心。
父母老了。尤其是父亲,腰弯成了一张弓,似乎随时要将自己发射出去。但他依然是一副好脾气,在母亲和我们姐妹面前总是乐呵呵地笑,仿佛吃了蜜糖一般。
八十岁高龄的父亲病倒了,是肝癌晚期。从医生严峻的脸色和欲言又止的神态中,我们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大家陪着母亲泪流不止。
昏迷了三天的父亲醒过来了,母亲拉着他的手贴到自己泪雨滂沱的脸上。
孩子她娘,别哭。父亲无力的手替母亲捋了捋额际的白发,轻声说,你跟了我一辈子,真是难为你了。
父亲喘了一会儿气,看着我说,东坡那块沙地,我年年种花生,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们娘喜欢吃花生!记住,那块地以后继续种花生。现在你们娘年纪大了,牙不好,要把花生煮软一些!
母亲听着,撕心裂肺地哭。
你们谁要是不好好待你们娘,我到了那边也会出来找你们算账!父亲说完,大叫一声母亲的名字,咯血而逝。那是我第一次听见父亲叫母亲的名字。
母亲也昏厥过去。
从此,母亲变得郁郁寡欢,常常拿着父亲生前用过的短烟杆发呆,不时闻闻,仿佛那就是父亲的气味。
尽管有我们姐妹的悉心照料,母亲还是在半年后的一个深夜走了。她的手里,紧紧地握着父亲的烟杆。那只手,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掰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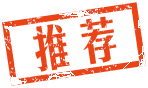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