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文璘 于 2018-10-26 10:42 编辑
民国四年,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龙泉寺,落魄失魂,人近疯癫。他在给夫人汤国梨信中意态悲切地写道:“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章本人扬过欧风,沐过美雨,政治惟新,思想激进,鼓吹革命。而治学上却信朴守拙,懂西学尽弃西学。精史学、文学、考古、金石、小学、朴学、训诂、音韵诸行当,门下弟子遍布寰内。梁任公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誉曰“清学正统派殿军”,意为学术之太宰也。
清末到民国,学术分三支。章太炎是其一,其二为康有为和梁任公师徒,其三是罗振玉与王国维两位亦师亦友者。王国维观堂先生承前启后,是现代学术的垦荒者和奠基人。以词章之学而论,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借用尼采和叔本华的悲剧说来解读中国古典名著,一举突破了“考证之眼”以及古典批评里重片段妙悟轻理论体制之局限。虽有牵强附会和误读之嫌,但启山林之功功不可没。越两年,即1906年他写《屈子文学之精神》已经以外化内、中西汇通了。再越两年,到了1910年的《人间词话》可谓是功臻化境,中西交融,通天人之际矣。惜先生在1927年自溺于昆明湖,一代天才,就此陨落。
继国维先生衣钵的是钱钟书先生。钟书先生倡大文化观,讲“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两部大作《谈艺录》和《管锥篇》。前者自谓“忧患之书”,实开比较诗学之先声。后者钩僻抉异,态度坚决亦绕指柔地告诉读者:南学北学之差,古今中外之别,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所谓差别,奠基于攸同,脱胎于未裂。没有攸同和未裂,差别便不存在意义。
同代或后辈卓识学者多认同钟书的大文化观。梁宗岱以中国的“兴”来理解西方的“象征”,佐证了中西诗学共通的文心诗眼,即共通的心理、智慧和审美情趣。朱光潜用“阴”和“阳”、“南宗”与“北宗”来比附康德的“崇高”和“秀美”。他的《诗论》一书聚焦中西诗的共同原理,以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同时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摆出两大值得关注的问题:“固有的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外来的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收?”
以上谱系草灰蛇线,但警警有力。然,若干年后竟成孤绝一脉。撇开建国后前几十年的学术荒原期不谈,80年代以降,伴随着现代化的呼声,西学重新东进。学者们如过江之鲫,趋之如骛,惟“西”不谈,惟“西”不用,惟“西”马首是瞻。因之,院校之内,夷学是显;学林之间,戎识为宗。致使,“假洋鬼子”之辈,汹汹作势,“二毛子”之徒,纷纷弄权。此时“中学”有累卵之危,“古典”有倒悬之急。
一二有识之士曾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北大钱理群先生,不附时,不跟风,坚持用现实主义的历史观来治《周作人论》。一肚子洋墨水的王德威赞其“用老方法同样取得新成就”。孙绍振先生,当年“三个崛起”后,发现西方学术重理论体系轻文本的顽疾,痛定思痛,转向“东方学”中找治学良方,独创“文学文本解读学”。文章老更成。然,上两位抱着原教旨主义的态度,有限的视野阀门到底堵不住洪水猛兽的泛滥。
此时,《诗的八堂课》和江弱水可以呼之欲出了。它的出现,不敢说是包源流,但足可综正变。我之所以不胜琐碎不厌其烦地追踪其谱系脉络,原因无它,因为关乎学理上“逻辑”和“历史”的方法论问题。不勾勒爬梳此就不能晓开合、明正法、识理路、具上乘。这亦是米歇尔.福柯所专的知识考古的学问。另外,对江弱水影响较深几本书,《文心雕龙》、《诗品》、《原诗》以及《顾随诗词讲记》等我是存而不论的。缘由是前三者系为古典,而《诗的八堂课》是中西合璧的比较诗学。为什么选晚清这个切入点?借用王德威先生的研究成果,晚清是中国现代性的萌芽,是被“压抑的现代性”时期。《顾随诗词讲记》确实有“出土文物”之新鲜,读之让人有烟霞共生之感,但只是些吉光片羽、零零碎玉。对江弱水的影响恐怕只在局部,不在整体;只在辞章,不在思想。
认识江弱水是从两本书开始的。《中西同步与位移》、《古典诗的现代性》。那时的江弱水白皙、瘦高,带着一副小眼镜。衡诗论文时表现出罕见的精细、从容、风趣、准确和算无遗策。天女散花一般的博学;信手拈来、抽丝织锦的智慧;八面玲珑而非仅仅两面三刀的做派。那时的他还是学术里的“愤青”,闹海的哪吒。在《中西同步与位移》中,他舍得一身剐,敢把穆旦(查良铮)拉下马。按照苏雪林攻击鲁迅的话说就是“一如老吏断狱,冷酷无情”。他历数列举穆旦模仿截取甚至抄袭奥登的种种例证,言辞激烈,证据凿凿,铁案如山,容不得穆旦翻供。《古典诗的现代性》简直就是他和学界开的一个大玩笑。当学界诸君们披肝沥胆地找寻中国现代性的源头时,有人把它定为“五四”;有人说是在晚清;也有人断言明中叶。而他江弱水君竟然从“彩丽竞繁,兴寄都绝;迤逦颓靡,风雅不作”的南朝,尤其是为闻一多所不齿的齐梁“宫体诗”中找到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肇始,真可谓是石破天惊。令多少保守派中人们摇头晃脑、咬牙切齿。可人家说得有理有据有节,几无破绽,你又不得不服。
T. S.艾略特有《诗的三种声音》一文,其中说道:“第一种声音是诗人对自己说话,或不对任何人说话;第二种声音是诗人对听众说话,不管人多人少;第三种声音是诗人试图创造一个戏剧性的人物在诗中说话。”如果以文类譬之,第三种声音自然是戏剧,第二种声音近于一般的散文,第一种声音无疑就是抒情诗了。如果和江弱水著作连在一起,《中西同步与位移》是戏剧,《古典诗的现代性》是散文,那么这部《诗的八堂课》则是抒情诗。还可以“罕譬而喻”,但不一定严谨,更不会“妙合凝也”。《中西同步与位移》、《古典诗的现代性》可比之康德的两大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1790年的《判断力批判》和2016年的《诗的八堂课》则可隔着遥远的时空作深情的凝望、相互的回响。
把《诗的八堂课》看成是自我独语的抒情诗,肯定会招致许多“江粉”、“江迷”们的不满和反对。哪怕它谈的是诗,尽管它明明是课堂的讲义。按理说应该是对听众的说话,属于艾略特所云的“第三种声音”的戏剧。其实,这只是牝牡骊黄的表象。
2016年的江弱水,人到中年。曾经了沧海,除却了巫山。阅尽了世间的盛衰之变,也历经种种冷暖自知的人情,真正步入现代艺术和学术的堂奥,也悟彻了古典的精髓。所有这一切都在他内心中涵容酝酿,“青”不再愤。在“中年写作”和研究中所表现出的不再是从前那种质拙直率的呼号,也不再是那种毫无假借的暴露,而是把一切事物都加以综合酝酿后的一种艺术化的情思。于是,他从外面的世界收返视听,回归内心。或作一个人巫语;或与心仪的杰作和大师们对话;或展翅高飞,哪怕没有天空;或独自舞蹈,哪怕没有观众哪怕一大片观众。
《死亡第八》,这是全书的结尾部分,也是全书的高潮与反高潮。江弱水谈“未知生,焉知死”的中国死生观;谈“向死而生”的西方存在主义哲学观;进而是“死亡美学”;最后以“《野草》作证”。他说:“现在,我终于可以讲讲鲁迅和他的《野草》了。”并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与不爱者之前作证。”《死亡第八》是深念之作,充满着冥想的气质。在江弱水意识的深层聚态里,有一反复出现的模式,可以宽泛地定义为文明与野蛮、活着与死亡、秩序与混乱、艺术与生存,以及前者受后者侵凌而衰颓崩解的过程,而最终归入永恒与变动中。所以全书是以“三兽渡河”的典故作结的。《死亡第八》是内倾的声音,有着音乐性的思维。或许正是因为“抄了生死的底”,是从悟彻死亡的孤独开始,迫于旁人无由窥测的心理压力而产生一种喃喃自语的内心交流。“未知生,焉知死”、“向死而生”、“死亡美学”、“《野草》作证”这些以节或联为单位的细部就像构成音乐作品中的“乐段”(section),充满着音韵的重复、对比与呼应。里面的各种“音型”因为密度、疾迟、高低、轻重的变化造成了节奏上的抑扬顿挫。思极深而不晦,情极哀而不伤,真真如王夫之所云的“九曲回肠,三迭怨调,讽之足以感荡心灵”,抑或如瓦雷里所谓的“文字的响度重于因果性”的音乐型自我独白体诗。
《诗的八堂课》是那种“老掉牙”式的结构。博弈第一、滋味第二、声文第三、肌理第四、玄思第五、情色第六、乡愁第七、死亡第八。乍一看以为是《文心雕龙》的翻版或者是后现代的“拟仿”或者“恶搞”,其实是江弱水在向伟大的经典作超越时空的致敬。在“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的今天,具有初读般的似曾相识,重读般的鲜活。全书伊始,江弱水说道:“此开讲第一回也”。横空盘硬语。让人疑似曹霑要开坛说法《石头记》。跟着又说:“却说到赌博和下棋头上来了”。这就是妥帖力排奡了。接下来就是江君长袖善舞的show time了。一些轶事、典故刚入心肠,便七分啸成机趣,三分归化自然,绣口一吐,就是半部诗史。每每又如此亲切谐和、不塞不滞,如隔壁老王又如邻家小妹。我们余犹未尽时,他雄辩的声音响起“有诗为证”;我们大呼过瘾时,江君却又兀自拈花微笑。敬文东教授有一段妙语评价《诗的八堂课》,现抄录之。“为这八个概念站台的、背书的,不仅有诗骚以来的中国古典诗词,还有欧美主要语种的主要诗人的主要诗作,更有一百年来的汉语新诗作品。一方面,它们联手为这八个概念尽心尽力地献上心悦诚服的呈堂证供,而且互不猜疑,齐心协力;另一方面,那八个概念也给足了它们抚摸、熨帖、安慰与滋补,并且不偏不废,一视同仁。当真个雷霆雨露都是圣恩啦!君臣之间相得益彰、心有灵犀的景象,主宾之间其乐融融、心照不宣的场面,实在令有心的读者大动其容,或‘一饭三吐哺’”。
江弱水的幽默是那种老派的类似于英国保守派的贵族式幽默。比如他论博弈型的诗人“博弈型的诗人是健身狂,容不下身上有多余的脂肪,非得要在肚子上掏出几块腹肌来。”钱钟书说过,所谓幽默只能让时空相隔甚远的二三子去体会;而所谓提倡幽默,本身就是一个幽默。江弱水对此知之甚深并得其真味。他的著述无不带着内敛而强烈的幽默感。你看,古典的现代性?滋味第二?声文第三?这不就是西装长辫子,小脚玩苹果手机的滑稽样?时代如此乏味,而这却令人振奋。
江弱水的器识堪为一流。《诗的八堂课》里,他讲情色和色情“色情是肉欲,以挑逗官能为能事;情色是肉感,以摇荡性灵为指归。所以,色情只诉诸本能,而情色却上升到艺术。我们可以把情色界定为一种感性,一种性感的感性。”他讲下半身写作“下半身写作严格说起来只是社会讽喻诗。身体写作是一种写作政治,是对自己身体的权利进行宣谕,把身体当作对抗世界的根据地。在语言配方和身体编码方面,它们都乏善可陈”。这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最好的对情色和下半身写作的解读。希伯来人云:“日光之下无新鲜事。”但要让光影翻出花样来,非打通任督二脉具备浑厚的纯阳内功者不能为之。
当然,《诗的八堂课》好处远不止这些。书话版诸子多为骏发之士,心总要术,敏在虑前,应机立断,领悟各有不同,议论多有华彩。不日,我将开单篇以评之,此就不再买椟还珠地作赘述。至于,罗列出《诗的八堂课》里引文资料的来源、训诂的出处、文献的正确与否则是一件味同嚼蜡的事情。遵敬文东先生教诲:大可交给学究们去经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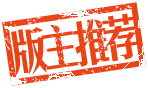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