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楚云婷 于 2019-1-20 11:07 编辑
如果我们将凝视的目光投向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的欧洲,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一幅世纪末的景观。欧洲各国的王公贵族和上流社会那些腰缠万贯的巨富们,置身于纸醉金迷的世界里,品尝着优雅和闲适,享受着快活与放纵,而底层的民众也在传统的惯性下埋首于自己的营生。这是个曾经于其生活过的人们颇感留念的时代,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曾对之作了一次动人的惜别。在许多人眼里,这是一段黄金般的岁月,整个欧洲在多少有些颓废的气氛中似乎歌舞升平。
没有几个人能料到一场大风暴即将横扫这一切,信仰的崩溃和继之而来的残酷战争,把人们为之坚信不移的人类不断进步的乐观幻想击得粉碎。不过,尽管一股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潮在灵魂深处涌动;尽管尼采已发出“上帝死了”的呐喊,动摇了两千年来西方精神信仰的支柱,但绝大多数人仍埋头行进浑然不觉。就在这表面繁花似锦的日子里,一位诗人的声音预言般地奏响了:
我犹如一面旗,在长空的包围中 我预感到风来了,我必须承受; 然而低处,万物纹丝不动; 门还轻灵地开合,烟囱还喑然无声, 玻窗还没哆嗦,尘埃也依然凝重。 我知道起了风暴,心已知大海翻涌。 我尽情地舒卷肢体, 然后猛然跃下,孤独地 听凭狅风戏弄。 《预感》
多么敏锐的心灵!像先知般地洞悉一切!诗人表明自己要坚强地驻立于大地,勇敢地迎接暴风雨的考验。在山雨欲来之际写下这首警世诗的作者,就是二十世纪德语诗坛最伟大的诗人奥地利的里尔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里尔克可谓生不逢时,当他迈步诗坛之际,那神性的光辉已开始从这个奢糜的世界渐渐隐去,大地开始变得荒芜,精神的领域充满着混乱。敏感的诗人在这迷惘中找寻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成了浪迹天涯的精神流浪儿,他痛苦地倾诉道:
小时候我没有家, 也不曾将家失去; 在世界之外的某个地方, 母亲将我生育。 而今我站在世界上,不停地 走向它的深处, 有自己的幸福,有自己的痛苦, 有一切的一切,却感到孤独。 我的祖先曾经显赫, 曾有过三支旺族, 曾住在森林中的七座宫殿里, 只是已经疲倦得扛不动族徽, 已经衰老得一塌糊涂;…… 他们留给我的遗产,我挣得的 永久权力是……没有归宿。 我不得不将它捧在手中,抱在 怀里,直到最后一息。 因为在这世界上, 我无论建造什么都会 崩塌, 就像建在浪峰, 波谷。 《最后一个承继者》
诗人的早年是不幸的,父母的不合与离异、母亲偏执的宗教信仰和虚荣、少年时代五年令人窒息的军校生活,无论灵魂还是肉体都饱受摧残。这使心灵异常敏感的里尔克更深刻地体会到精神无所归宿的的境遇,他无法忍受家族对其人生强制性的干涉和规划,竟在21岁毅然离家出走,独自跑到幕尼黑圆自己文学之梦,从此失去了家庭的资助。
不过,这位伟大诗人的文学生涯却是以平庸开始的。初涉诗坛的里尔克深受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在那种主观情感的喧泻和多愁善感的模仿中,他写下了一些不成功的诗作。在他蜗居幕尼黑与当时的才女莎乐美相爱后,这位杰出的女性对里尔克的影响和指导,才是他人生道路的转折点。俩人两次结伴同游俄国的经历,使俄罗斯成了里尔克又一个精神故乡。他深深沉浸在陀斯托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世界里,孕育着他内心的丰富和深刻。 . 与萨乐美分手后,里尔克和女雕塑家威斯特霍夫结为伉俪。不久,里尔克独自去了巴黎,结识了雕塑大师罗丹。有一段时间他还成了罗丹的秘书,与之朝夕相处。正是在与罗丹的交往中,他领悟到了艺术的真缔和勤奋“工作”的重要;而另一位绘画大师塞尚的作品也使他大开眼界所获良多。正是在这段时期,里尔克学会了不以个人情感而用超个人观点写作,使自己完全面对现实事物。他开始写出一生中重要的作品,他独特而又迷人的文字从下面这首诗中可略见一斑:
在铁栏前不停地来回往返, 它的目光已疲倦得什么都看不见。 眼前好似惟有千条的铁栏, 世界不复存在,在千条铁栏后面。 柔韧灵活的脚迈出有力的步子, 在一个小小的圆圈中旋转, 就像力之舞环绕一个中心, 在中心有一个伟大的意志晕眩。 只是偶尔无声地撩起眼帘, 于是便有一幅图像侵入, 透过四肢紧张的寂静 在心中化作虚无。 《豹》
这首意味深长的诗作,带给我们多么奇妙而富于诗意的感受!蕴涵于诗中的寓意何等深邃动人!我们今日这些困在大都市钢筋水泥中的生灵,与那只圈养在铁笼子里的豹子何其相似!
往后的岁月里,里尔克佳作频出。他的长篇小说《布里格随笔》达到了高度的艺术水平,而他的组诗《献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则完美得令人惊叹。但最为诗人呕心沥血,创作时间最长,并臻于诗歌艺术顶峰的,无疑是他那首震撼人心的长诗《杜英诺悲歌》。 . 即使不说里尔克一生穷困潦倒,但他一辈子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却是事实。好在那个年代王公贵族们赞助艺术家的传统遗风还未消失,一位通情达理和颇具才情的贵妇塔克席斯侯爵夫人,慷慨地把她拥有的一座位于瑞士名为杜英诺的城堡提供给里尔克居住和写作。一九一二年诗人就在这座城堡里开始了他为期十年的《杜英诺悲歌》的创作。从这时起他超越了自己“咏物诗”的阶段,以新的面貌直叩人类生存的底蕴,进入高度哲理性的诗化探索。
《杜英诺悲歌》由十首相互呼应的诗歌熔铸而成,这一宏伟的佳构几乎囊括了人类生存所面对的所有重大主题。让我们屏息倾听那如同天使般的声音吧:
谁,倘若我叫喊,可以从天使的序列中 听见我?其中一位突然把我 拉近他的心怀:在他更强烈的存在之前 我将消逝。因为美只是 恐惧的开始,正好我们仅能忍受者, 而我们又如此赞赏美,因为它冷静地蔑视着 欲把我们粉碎。
这一开篇就近似绝望的追问,直逼诗人存在的价值。在洞察一切真理的天使们面前,诗人不由地怀疑起自己的诗歌能否有可能揭示存在的奥秘。那诗人为之歌颂的美也因为难以企及,它作为永恒真理之光隐藏在黑暗中而令人恐惧。在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时刻,诗人并没有逃向彼岸的世界,而是坚定地伫立于此岸!
我们在自己解释的世界里 不能有在家的信赖,或许遗留给我们的是山坡上的一棵树, 我们日日可以重见:遗留给我们的是昨日的街道 不良的习惯上的忠诚, 这正适合于我们,而就此永驻, 不再离去。
爱情是无数诗人歌咏的对象,里尔克一生都尊重女性、热爱女性,自认从她们那里得到了丰厚的贈遗。他在男女关系上深刻的洞察力,揭示了爱情美妙的面纱下真正的本质.,男性在情欲的支配下那种黑暗的骚动令人惧怕,他写道:
歌咏情人是一回事。可是 歌咏那隐藏着罪恶的血腥的海神,是另一回事。 她从遥远认知的那青年恋人,他自身知道什么关于情欲主宰的事? 情欲的主宰常从青年的寂寞中, (在少女给予青年以抚慰之前,她常不存在似的) 啊,从那不可认知的事物滴落,抬起神样的头部 召唤着夜向无终止的骚动。 哦,血腥的奈普顿海神,哦,恐怖的三叉戟…… 哦,从螺旋状的贝壳吹来他胸中扇起的暗黑的风 听啊,夜如何把自己弄成坑洼与空洞。
男性的爱只是被情欲所催生的幻觉,最后的时刻总是以女性被伤害而告终,而最好的结局也是因在女性的引导下男性被拯救所致。为此,诗人告戒女性道:
而你自己,你知道什么,你在情人的心中 唤起洪荒时代。何等的感情 从逝去的人生激动起来。何等的妇女 在那里憎恨你。什么样的男子 你从少年的血管中把他鼓舞起来呢? 死去的儿童求你……哦,静静地,静静地, 为他做一件爱的信物,可资信赖的日常工作吧…… 引导他走向花园,给他以 夜的优势吧…… 抑制他……
这上个世纪初发出的浩叹,至今读起来仍令人惊悸。在当今欲望横流的世界里,那古老的情爱悲剧正发疯似地上演着。男女的结合充满了交易,欲望的满足成了唯一的目的。家庭在摇摇欲坠,昔日被视为神圣的爱情逃之夭夭,人们扯去了这最后的遮羞布,成了赤裸裸的情欲奴隶。
里尔克羡慕动物,对它们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和谐共存无限神往,他赞赏道:
动物以睁大的眼睛,凝望着 开放的世界。只有我们的眼睛 反逆似的,有如罗网,在它四周围置着, 环绕其自由的出口。 我们只有从动物的面容去认识 外界是什么;因为既使幼小的儿童 我们令他转向且胁迫着向后凝望 造型的世界,而不是在动物的眼光中 如此深邃的,开放的世界,免于死亡的威胁。 只有我们凝望着死亡;而自由的动物 始终把没落置于身后, 神在前引导,当行进时,就走向 永恒,如喷泉一般。
而我们这些所谓的“万物之灵长,”却在技术文明所竖起的铁墙里与大自然隔离。人类怀着征服自然的狂妄幻想,肆意地践踏着神圣的大地,而被人类所污染的大自然也毫不留情地报复了我们,历史已走到了人类稍不留神就会遭到灭绝的地步。
回归自然,拥抱大地,已不是我们可有可无的某种奇思异想,而是在徘徊于万丈悬崖边上的人类一项绝对的生存律令。也只有如此,人类才能在此岸筑居,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
我总有一天,在严格洞察的终结, 向首肯的天使们高唱出欢呼和颂扬。 明晰地击打着心的仵槌, 没有一支落在柔弱、犹豫、或者激动的弦上。 籁籁泪下的面容,使我 更显焕发:朴实的清泪 绽放着。啊,那时,你们将对我多么亲切啊! 忧愁的夜夜哟,无可慰籍的姊妹哟, 我不向你们下跪, 让我承接,我不委身于你们松弛的发丛, 使自己更加松弛。我们,苦难的挥霍者啊。 我们的视线是如何的越过苦难,窥入伤悲的持续, 或许不至于终结吧。可是,苦难真的是 我们耐寒的树叶,我们深浓的常青树, 隐秘年代的一个季节……不仅是季节…… 而是场所、村落、营地、地面和宅第.。
人生在世没有一条平坦的道路可供选择,而苦难却如影随形般地陪伴着我们无法规避,勇敢的人们恰恰在苦难的淬沥下酿成至醇的美酒。在漫长和艰难的探索后,诗人终于能面对天使无愧地歌唱了,诗人视苦难为自己的荣耀,只有承担苦难而前行的人,才能走进神圣的存在。驻足于大地,承担起苦难,这就是诗人留给我们最终的启示。
说不尽的《杜英诺悲歌》!即使像这样管中窥豹似的一瞥,也使我们的心弦为之强烈地颤动。它博大精深的境界,既令人着迷又留下不少神秘和困惑。诗人的思想也始终充满矛盾,他时常悖论式地思考和倾诉,即使在他为自己亲手撰写的墓志铭也留下了一个永恒的谜团:
玫瑰,呵,纯粹的矛盾,乐意 在这么多眼睑下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睡梦
诗人因白血病于1926年去世,那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了,当时遍地废墟,满目疮痍,人人为失去信仰而焦虑不安。这是一个被美国女作家斯泰因称之为“迷惘的一代,”诗人的吟唱无疑给人们带来某些希望。
历史何其相似!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又一次徘徊在人类生存的十字路口上。如今重温里尔克那启示录般的诗篇,好似长夜里天边露出的一道晨光微熹。在我们等待着拯救的苦闷时刻,请牢记里尔克的忠告: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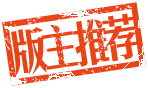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