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夏日荷风 于 2019-2-20 09:42 编辑
此刻,我静下来,收集一滴又一滴干净的晨露 ——曹文轩小说《青铜葵花》中那些闪烁着的美
葵花,不仅仅只是一个长相干净,文静清瘦,乖巧懂事的小女孩,绝对不仅仅是这样。在我看来,她是大自然中的一件尤物。在暴风骤雨之中,在阳光灿烂之时,她自自然然地生长,孤独寂寞地生长,向着太阳生长,向着月亮生长。仿佛一株春草,亦仿佛一棵垂柳,生长着生长着,她就同日月星辰一样有了属于自己的灵性,有了属于自己的语言,她是那么自然优雅地走近一朵金色的野菊花,走近一只落在树上的乌鸦,走近一只落在大麦地上的长着长脚的大鸟……人类应该是大自然的客人,在彼此尊重的心理中走向更深层次的和谐,而葵花,分明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部分。她那纯净无邪的心魂,能够透视一切无声和有声的世界,从而达到完全的融入和抵达。纯净无邪的心魂,是一切大美的孕育和诞生地带,是一切穿越苦难的美丽银锁,也是一切深刻暖心的故事的起点和背景。孤独和灵性,是一切伟大艺术作品的精神的发源地。所以,从某个角度说,与其把葵花看做一个长相干净、文静清瘦、乖巧懂事的小女孩,我更愿意把她看成是发出天籁之音的潺潺春水,余味未尽地消失在了远方一片葳蕤的丛林。
故事开头,小葵花的出场,那么自然,那么孤独,那么悠然,那么特别。干净的心,干净的苦难,干净的孤独,让我感觉到,接下来,势必有一场润泽天地的鹅毛大雪出来,寒冷了土地的同时,又润泽了土地,温暖和美好了整个世界。
唯有一个孤独的灵魂,才能真正与另一个孤独的灵魂相遇、相知。五岁的世界,在寻常孩子的眼里是朵花儿。五岁孩子的世界,该是一朵花精彩而完美的放香与绽放。可这个于大火中失音的青铜,他眼里的这朵花注定失去了一种曼妙。痛苦会让一个人过早地成熟,哪怕是一个五岁的孩子,他尚未形成思想,命运却赋予了他茫然与孤独。可是,世界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当花朵在青铜的世界里失去了一种曼妙的姿势,另一种更深情的姿势却伴随着他对孤独的理解日益清晰。这使得他怀着一种更浓烈地爱去看生活里的花朵与花朵里的生活。
一颗干净的心加另一个干净的心等于什么?绝对不只是干净的量变,而是一种境界的提升。干净的心是剔透的晨露,当一滴晨露与另一滴晨露相遇,也许正是骄阳渐起,也许正是春意盎然,可那只是外部,那彼此相逢的剔透与惊喜,足以撑起两个干瘪而孤独的世界,足以营造一种声势浩大的隆重开幕。
听听这些尽情而温暖的表达吧: ——葵花的出现,使青铜知道了这一点:原来,他并不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孩子。 没有语言的表达,善良纯洁的孩子,天然生发出一种哲学家的情怀与诗人的敏感。他们已然在用目光神交,他们的相遇已然有了一种旷古的深刻。
青铜葵花的相遇相知,是一种艺术的必然,也是一种生命的必然。冷暖相依,苦难与幸福相连,是作者曹文轩通过这个故事,呈现给所有读者的一种温情暗示和美好寄寓。
而小说中葵花的父亲,则是作者派去直抒胸臆的。葵花父亲,这个痴迷葵花痴迷青铜葵花痴迷艺术的艺术家,其对现实世界与艺术世界的亦真亦幻的感受,既是对接下来故事情节的顺接铺垫,又是对小说主题的最直白的揭示。
葵花的父亲,一个极具艺术气息的温情的父亲,一个不幸而又幸运的艺术家。艺术成全了他,又毁灭了他。艺术充盈了他的世界,又将他从这个世界完全地剥离。作为所在城市一位著名的雕塑家,他最得意的一幅作品就是青铜葵花的雕塑。他觉得,“暖调的葵花与冷调的青铜结合在一起,气韵无穷。”这么看来,暖调的葵花与冷调的青铜结合在一起,既是一个愿望,又是一种宿命。葵花与青铜的相遇已作为葵花父亲的潜意识存在久远,这是一个自然而神秘的铺垫,这样的铺垫,让我感觉,一切美好的相遇与诞生,都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都是所谓的缘来与缘起。
父爱也温存。常常觉得,葵花岂不正是父亲心头那朵最灿烂的葵花。因了这朵葵花的滋润,一圈圈散发着暖度的爱的涟漪从这个孤独的艺术家的心头发散出去,孤独就此得到了疏散。葵花,既是在他随手可触的现实里,又在他虚无缥缈的漫长梦境里。艺术和现实就这样相互渗透和融合在了一起,成就了一种无法避免的哑然的悲剧之美。
读到现在,我感觉到,无论书页里的任何一个文字,都散发着一种阴沉的冷郁,它们氤氲一起,产生了一种似乎非要把什么推到一个极致的强大的艺术背景。一种让一切哑然的悲,一种让上帝也安静下来的静,聚集着,缠绕着,相遇着,也酝酿着。柔软在一种无声的气息里滚动,这是一种类似打秋千的滚动,这种滚动因变异而生动,因柔软而席卷,因席卷而生发着期待,一颗心从这里路过,就像一双眼睛在黑夜里凝视,眼神里跳跃着喜悦在凝视。
你相信宿命吗?你相信形而上吗?我小的时候,真的不信。可是,随着阅历的增长,当我发现生活里、世界中越来越多地出现的那些无法解释的事件和现象时,我真的相信了一种冥冥之中的天注定。对于我们无法掌控的生死,对于我们无法解释的生命的起源,以及一些灵异事件,我们只有把一切解释权教给宿命和上帝。就像青铜和葵花的相遇,就像寒冷的冬天和温暖的春天的相接,就像一切大难和大美的交融,这难道不是上帝献给不断承受苦难的人类的馈赠和礼物吗?
经过炼狱之后的生命,势必呈现出一种空灵的美感。
一个七岁,一个十岁,一个小女孩,一个小男孩,尚未涉入真正的生活,却用心品尝到了真痛苦。这样的一颗心,会因期待而多么孤独。这样的两颗心,会因相伴而多么幸福。很多时候,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两颗小小的心脏,两个因苦难生活而羸弱的心脏,因一场相逢的甘露,在尽情甚至肆虐地舒张、伸展。仿佛他们这么多年的经历和存在,就是为了这样一份美好的等待。虽然不是春天的季节,我却看到大麦地上的野花忘乎所以的开了,开得漫山遍野,开得映红了云彩和蓝天的脸。开得大麦地上的一切都黯然失色,有那么的一些时刻,我甚至想伸出手,插入紫色的潜意识,去抚摸葵花那因雀跃而飞舞的发丝,去捏捏青铜那因目光闪烁而倍加可爱的结结实实的脸蛋。
我想,是那个名叫苦难的东西,让青铜和葵花如此真切地体会到了幸福的内涵。这么说来,苦难真的有一张凶险的脸吗?真的散发着一种阴冷的目光吗?苦难那阴沉深色的外衣,如坟墓般肃穆,如谶语般煞气,难道它这样的一副皮囊之内,藏着的却是一颗名叫幸福的种子?难道苦难和幸福,真的就如姊妹般亲密?它们彼此相依相融,让我瞬间感觉,它们的区别,或者就是自己的左手和右手,它们也许拥有着一个共同的躯体,拥有着一颗共同的心脏,它们之于我们,或者就相当于我们眼里红和绿、黑和白、深和浅这样的两种对比色彩。或者比这样的亲缘还要近。苦难并不可怕,苦难于我们,也许只有一个善良的目的:炼狱生命、提纯灵魂,走近纯粹,感悟大美。
贫穷也好,残疾也好,作用的都是物质的感官。而这些,与内心对快乐的接受没有必然的关系。一个健康的灵魂,会永远将心灵的方向调试为面向太阳,就像冥冥之中,大自然对一朵葵花的神秘调控。你看,青铜和葵花,沐浴着连绵的雨丝,到水渠用网打鱼,他们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葵花捡大鱼,又捡小鱼。他们在雨地里一阵狂跑,又故意跌倒。“两个小人儿在田野上走动、嬉闹,大麦地人的心里会荡起微微的波澜,那波澜一圈一圈地荡开去,心便湿润起来,温暖起来,纯净与柔和起来。”是的,大美与大爱,总是从无邪的纯净里孕育和诞生的。
那个时刻,在大麦地人的眼里,是两个小人在雨中奔跑吗?是两个小人儿在低垂着脑袋在秋日葵林里游走吗?是,却又不仅仅是。那一刻,冷调的青铜与暖调的葵花,都在吐蕊,都在绽放,在雨中,在葵林里,他们都成了追逐太阳的孩子,他们那份单纯的快乐,绽放着童年的美丽,也释放着人性的本源,也许大麦地人没有高深的文化去总结,而他们却会用剔透的眼神、无羁的心灵去感受。那个时刻,葵花和青铜,这两个单纯着快乐的小人儿,他们无异于一条清澈小河里的鱼儿,无异于一个低垂着脑袋的葵花,无异于一片浸润着绿色的苇叶。那时的他们,正和自然界里他们的兄弟姐妹一起,悄然地静默太阳,无声的礼赞生命,幸福地传达爱意。这是一种真正的诗情,葵花青铜以及那些被他们温暖起来的大麦地人,是浩渺宇宙、茫茫众生里一份真正的诗情啊。
在我看来,此刻,这部小说又达到了一个抒情的高峰。
幸福,于凡人,的确称得上一个奢侈的字眼。小说里常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人生岂不如此?有朝一日,当我们充满诗意地去回首往昔时,可曾发现过你生命的某一段落如微澜的死水吗?绝对不会的,且不说多事的中年、懵懂的青春,哪怕是在清澈的童年里,谁的眼里不含着几滴无以言说的泪水呢?
在我眼里,幸福好比理想,它是一个目标,我们只能走近它,却无法凭借感受去完全地穷尽它。哪一天世界上有了绝对论,彻底没有了相悖的矛盾论,你才有资格发表某某真幸福或者你真幸福的言论。否则,一切都是对幸福本意的误解、扭曲或支离。
我们平时所说的幸福,应该是更大程度上接近了幸福。
幸福的本质是什么?首先,我觉得它应属精神范畴,更多地指向心灵。其次,它更多地体现在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份彼此笃定、和谐、温暖的内在感受。
在贫穷的青铜葵花家,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名词:一个在最大程度上靠近幸福的名词。
的确,贫穷是卡在青铜家喉咙里的一根刺。是一根真的刺。它会将肉刺出血,它会让人不住地咳嗽,甚至哮喘,站不直身体佝偻着腰身。被暴风雨席卷了的窝棚,三月蝗灾之后的饥肠辘辘,堪称天文数字的奶奶的医疗费用,一次又一次将贫穷的危害做了最直白的诠释。也许你以为幸福于这样贫穷的家庭来说是绝缘体。可是,我不这样认为。我脑海里不止一次地浮现出发生在这贫穷之家里的一幕幕:冬天,青铜采芦花、捶稻草;奶奶搓绳;葵花将奶奶搓的绳子绕成团;爸爸妈妈编织;青铜风里雪里去镇上卖。青铜带着葵花去稻香渡看马戏,为了让妹妹看到马戏表演,固执地蹲到地上,让妹妹骑到自己的脖子上,后来身体开始晃悠,眼前一片漆黑,有一阵,身子脑子里空空,身体没有了重量,在黑暗里飘动着,却又不倒下来。有一次,葵花演节目,需要一条银项链,家里买不起,小男孩青铜,竟然独出心裁地为妹妹做了一条冰项链,成为整场演出最令人瞩目的焦点。葵花的奶奶,为了给孩子们做上棉裤棉袄,谎称去东海妹妹家探亲,实则去那里打工,摘棉花,挣棉花,结果不堪重负,晕倒在棉花地上从此再也无法起来。小葵花,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故意将成绩考砸,想就此辍学,失败之后又悄无声息地去油麻镇,坐船去江南捡银杏,为奶奶挣医疗费。……一个又一个爱的涟漪,从这个贫穷的家庭接连发出,被我动情的心接收后,让我感觉到这个家庭里有一种和幸福最接近的温情,苦难中的心灵相依,为了共同的目标而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彼此深深的牵挂,忘我的牺牲。我想,即便是每天多卖出了一双芦花鞋,即便是每天多攒了几堆建房的茅草,这些彼此相依的人们的内心,也注定会生发出许多笃定的坚强和温暖的柔情。笃定,坚强,温暖,柔情,我想,这些词语的组建交融,该是最接近了幸福的内涵吧。
最后,葵花走了,离开了大麦地,离开了青铜一家。她返回了父亲生活的那个城市,开启了一段崭新的生活。
不管葵花最后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不管以后她会选择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我想,她的心,终会留在这片偏僻的大麦地里。终会留在这个为她精神打上深刻烙印的贫困之家。离开了大麦地的葵花,我想,她的一生,注定无法遇到第二个青铜,虽然她也有可能迎来自己精神世界的葳蕤,但是,在她的世界里,再也无法遇到那片和青铜一起低垂着脑袋走来走去的葳蕤的葵林,她已把这片最葳蕤的植物森林,永远地留给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青铜,那个大麦地上有着善良的爸爸妈妈和奶奶的青铜哥哥。
青铜会说话了,他说出的第一个词就是“葵——花——”
这朵开在他生命里的葵花,注定会诞生出一个美得像花一样的奇迹。
这花的名字就叫什么?我把它叫做温情。后来想了想,它似乎也可以有个更华丽的名字——大美。
那么,苦难的最深处是什么?就是一朵名叫温情的花啊。就是一朵能够诞生奇迹的大美之花啊。
所以,爱这个苦难深重的世界吧,爱这个世界里的种种苦难吧。有滋有味地爱着他们,享受着与他们走近或者走远的过程,就仿佛欣赏着一朵花从孕育、含苞到绽放的过程。
这样的你的一生,注定会馨香满园。这样的我们的世界,注定会诗意盎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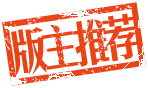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