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孙姜 于 2019-5-22 09:21 编辑
打木耳段,之所以叫“打”就是用专门的木耳锤子加一个空心铳子在柞木树杆上打眼,用漏子塞进木耳菌后再把铳出来的木芯装回去。木耳段种好后,就选个开阔的地方摆好,不断地浇水,浇水的同时盼着木耳出生、看着木耳长大、等着木耳收获,这当时是山里最来钱的产业。产业是别人的,我们只是在“打”的过程中挣几个小钱儿。
忧郁的山楂
离开学校的第二天,就跟着爹去离家六十里的三块石林场,五叔在那儿跟上了一个打木耳段的队伍,叫上我们一起挣钱。
到的那晚儿,爹和五叔还没喝完酒我就躺下了,五叔在酒里跟他老哥比比画画地描绘着我永远看不到的五婶:“不是天仙我不娶,宁可孤单。孤单有孤单的好处呀,哥你不懂……”也不知道五叔还写不写诗了,我没有心情问这些。我算计着,能不能多挣点钱,回家买塑料扣个大棚种点菜,卖菜应该能挣不少钱吧,攒够了钱就重新回学校去,不仅要把初中读完,还想接着读高中,念大学。
第二天早上,我被鸟叫醒,这里的山可真高啊,砬子也像五叔诗里写的那般帅气。在一个山坡上蹦达够了,我捧了几株半开的冰凌花回家。我在院子里栽花的时候,进来一个小伙子。小伙子跟五叔交待好第二天上工的时间和地点,就蹲下来帮我往那些瓶瓶罐罐里浇水:“你这么稀罕花呀?”他的眼神儿都在我的脸上,瓶子里的水溢了一地。“嗯”,我低低地应了一声,头都不敢抬。头没抬也看到了爹的白眼,我是从爹不正常的咳嗽声里看到的。
小伙子叫大龙,大龙爹是揽活的。无论大龙在眼前如何飘来飘去,我就是不抬头。“才十六岁的丫头片子,你给我轻点儿嘚瑟。”爹这句话到底啥时候说的,我想不起来了,或许他根本就没说。这些年给娘治肾病,家里有还不完的饥荒。
头一份活是给老齐家干,五叔他们戏称这个活叫“齐活”。爹负责打眼,我负责塞菌、压盖,紧着忙活,一根木耳段挣3角,一天下来只打了不到100段,用五叔的话说,俩不顶一个。“齐活”不好干,东家好像长了八只眼,天天骂声不断:老李你个鳖孙,铳子得直着往下凿——奶奶的老李婆子,你那木耳菌塞实成点,那眼儿都空壳啷儿呢你就往里钉盖儿,还能长出来木耳吗?你家老李不下籽儿,你就能养孩子呀——老袁头儿你个窝囊废,你在那儿给柞木杆儿挠痒痒弹脑瓜崩解闷呢——王八犊子大龙,你他娘带了一帮什么人过来——
“齐活”一共干六天。接着是十二里地外的“刘活”,计算方法是完成一袋菌挣一块伍角钱。这时候的我已然一个行家里手。锤起锤落,我听到的似乎是驰向远方的哒哒马蹄,不知咋的,马蹄声里还飘忽着大龙清澈的目光,于是,我手里忙着,脸上笑着。一天下来,我心想今天保证能第一,这次来的大都是跟我们一样的父女组合,三块石的那些大老娘们出不来。可晚上一统计,我和爹还是最后一名,我百思不得其解。
男人们住在临时搭起来的工棚里,我和另外三个女孩子住在东家的西屋,有火炕。早上,刘婶子的大花卷跟她的笑脸一样香甜温暖,绿是绿、黄是黄,喜兴的菠菜蛋花汤也管够。再干活,我用第三只眼瞟着别人。妈呀,可不好——小丽边干活边在脚底下挖坑,一袋一袋往里埋菌;小红把菌碾碎放到装盖儿的簸箕里,跟着木屑草叶儿一起簸了出去;小娜腿快,不时去山后面扔几袋……看得我手直哆嗦心直疼。尽管我自己一粒菌也没糟贱,可晚上面对刘婶子的嘘寒问暖还是觉得心虚,饭也不好意思多吃了。
第二天、第三天,那三个女孩子还那样忙着,而我手里忙着眼睛可再也不到处看了。后来,刘大叔从山坡下捡回来一大塑料袋子木耳菌,脸是黑的。
下午的时候天也是黑的,然后下雨。不能干活了,四个女孩子去逛林场唯一的商店,“蓝天小百”。我们围在化妆品柜台前挪不动脚了,变色口红最是抢眼,从里绿到外的小东西,怎么涂到嘴上就是红的呢?可是,三元钱的问价瞬间埋葬了我们这帮小丫头片子的好奇心,店员都没让我们碰一下。小丽要了一把粉红的小塑料梳子,刚要试就被喊住了:“你试完了我还能卖去吗?”那语气!我在一边儿都觉得臊得慌,小丽不觉得,小娜也不觉得,小红也不觉得,依旧叽叽喳喳。我的目光粘在摆在靠着窗户的一块小方镜子上了,镜子里天蓝云白,再看,还有一双水汪汪的眼睛。
走出“蓝天小百”,天真就蓝了。她们每人买了5角钱的山楂,其他的水果都太贵了,又不禁吃。我也买了2角5分钱的,每嚼一颗都酸得心头直颤。
回到东家家里的时候,我看见大龙正把一大把半开的鞑子香放到西屋的窗台上。我问过刘婶子了,用大棚种菜,本钱大着呢。我把最后一颗山楂塞进嘴里,心里着实有些忧郁。
隐形的课本
小颖家在五叔的前院,小玲在后院,一起上下工,很快就熟悉起来。干活时也明里暗里比着,身上多了一股劲儿,手上多了几分巧。
早上,会有一个四轮子来接我们上山,开车的是个半大老头儿,稳稳地把一天的精神抖擞和一车的欢声笑语送到了山顶。上车时他曾经扶了我一把,我记得他通透的目光。晚上,他再从山顶把我们接到山下,接回来的可能就是一天的疲乏和一车的沉闷。打木耳段儿,必须眼到手到,一点儿也不能马虎。稍不留神,少挣了钱不说,咱也丢不起那人哪。
大老李家的活儿整整干了半个月,下一份活儿是赵大凯家的,中间隔两天。终于不用早起了,我睡呀睡。被五叔喊起来吃了口饭,又一头拱到炕梢,我要把这半个月缺的觉都睡回来,把一身的疲劳都睡走。
“花儿,起来,咱们去小静家玩去。”我迷迷瞪瞪地睁开眼睛,看到的是小颖和小玲。小颖的长发披下来,用一条白手绢系着,小玲穿套土黄和深蓝相间的运动服,都很抢眼,我一下子醒了过来。
“好容易歇两天,你们不好好睡觉,打扮这么漂亮干啥呀?”
“起来,咱们去小静家玩去。”小颖白脸蛋儿上那几颗雀斑,这会儿个个俏皮。
“小静是谁?”
“小静是每天接送咱们上山下山的那个小伙子的姐,住在道北。”小玲的大眼睛和小嘴巴,这会儿也圆得妖娆。
我五叔居住的牤牛屯,跟三块石林场只隔着一条大道,道南道北,是两个世界,道南住的都是低到尘埃的农民,道北住的就都是神采飞扬的林场工人。
“接咱们的,不是一个高个子老头么?”我被她俩彻底弄晕了。
“唉呀,花儿你真是个糊涂虫。老头只送了一天,第二天起就是他儿子接送咱们了。这你都没注意?”
“嗯哪,那小伙可帅了!”
说到那个小伙,她俩的眼里都放着光。我被余波电醒——她俩是不是都喜欢上了人家?唠一唠就知道她们已经打听到小伙子有个姐姐叫小静,于是要去找小静玩。
“不认不识的,去跟人家说啥呀?你俩趁早打住。”
被我泼了冷水之后,她俩开始互相埋怨。
“是小玲非要去的,我无所谓。”
“小颖你说这话亏不亏心?小静家的情况,可都是你缠着你表姐打听出来的。”她们不欢而散,我继续睡觉。
下午,小颖进院时我正洗衣裳。她二话不话,伸手就干,三下五除二就晾满了一院子。
“花儿,走,陪我去小静家!我想好了理由,你不是一直嚷着要看初三课本么?小静读高中呢。”
小静家是长长的一趟红砖房中的一户,院子不大,立砖铺成人字形的路面儿、柈子垛、储煤栏都很齐整。进屋,半截白色门帘,铁脸盆架,高低柜儿,处处都是道北气息。只是小静很冷淡,任小颖像一只呱呱鸟儿,她只“嗯嗯”着,脸上一点儿表情都没有,像那个静静地垂着的白门帘。“初中课本早都借给别人了,你们来晚了。”她弟没在家,在小静高强度的漠视下,小颖终于闭上了嘴巴。出了门,长头发一甩,回家了。
刚来得及把院子里的衣服翻了个儿,小玲就来了,也拽着我陪她去小静家。“花儿我想好了,咱们去小静家给你借课本,小静是高中生呢。”
“小静的弟弟没在家,咱还是别去了。”
“你怎么知道?”
“刚才我陪小颖去过,也是说借课本,你俩还真是英雄所‘借’略同。”我把声音低下来,使劲儿把笑憋了回去。
“说不定现在就回来了,走!”小玲拽得我胳膊生疼。
“可是,小静都说初中课本都借出去了。”
“那就借高中课本!”
去了,小静依旧冷冰冰。有一个帅气的弟弟,她是不是时常要应付这样不着四六的女孩子?等到小玲也讪讪地从道北回来,就到了晚饭时候。
这个没借到课本的晚上,天上也没有月亮,星星稀稀拉拉地散落在漆黑的夜空里,仿佛个个都有心事。我在院子里独坐,我努力这一春,还了家里的欠债还够不够明年的学费?我想念我的教室、老师和同学,想念读书的日子。有悠扬的口琴声从道北飘来,断断续续的音符感伤忧郁,听得我流下泪来。会不会是那个出现在我生命中十四天、我却视而不见的帅小伙吹的?他到底有多帅?唉,他帅他的,我这只丑小鸭只关心什么时候能有新课本,因为念书是我走出大山唯一的路。
第二天,小颖和小玲是一起来我五叔家的。昨天还像一对冤家,怎么这么快就好了?
“花儿我告诉你,小静她弟有对象了,听说是林场会计的女儿。”小玲把一双大眼睛瞪成牛铃。
“嗯哪,我表姐说的,长得又黑又矬!”小颖把辫子甩到脑后,仿佛特别解气。
“道北的事儿,咱们还是别管了。明天几点出工?”
遥远的校长
黑熊出现时,天光渐暗。难得露面的太阳已经收走了最后的余晖。草,树,山场,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煮挂面时我唱着歌,不仅是今天多做出来两袋儿菌,更是因为有人为我的生活注入了新的希望——东家郑大叔说,只要我给他好好干活,干完活就带我去见林场中学的校长!
放木耳段的场地在山里,离村子远,为了每天多出活,东家安排我们住在山上,几个用木头杆儿和老旧混浊的塑料布围起来的窝棚里,星星常常从一个个破洞探进头来看窥视我的窘态。临时床铺是用种木耳的杆儿垫起来的,因为是一截一截的,所以叫做段儿。白天干一天活,晚上躺在“段儿”上面,算是全方位按摩,第二天早上起来,每一根儿骨头好像都被种木耳的钉锤折腾了一夜。
四叔是瓦匠,他在的包工队揽到一个盖房子的活儿,喊爹去当小工,妈就顶替到山上来了。妈的肾病那么严重,这样的劳动强度和住宿条件,能扛得住么?
离小窝棚大概50多米远的坡下有一条小溪,我们就用那溪水做饭。做饭也特别原始,在窝棚门前用两根木头支起一个焖罐子,在里面煮点简便的吃食,大部分时候是煮挂面。虽然艰苦,倒也有趣,那是头一天来时的感觉。等活一累,趣味很快就消失了,可是我仍然乐,很快就能见到林场中学的校长了呀!
黑熊来时,一点儿征兆都没有。那天,我在锅里加了妈妈取水时顺手从沟边采来的水芹菜。取水这活本来不应该辛苦我妈,可是我实在是怕。刚来的那天我去打水,草爬子在小路上树枝和树叶上、草茎和草叶上都挤成了串儿,直往我脖子、裤脚里钻,吓得我再也不敢去了。草爬子,学名叫蜱虫,它的大小类似于虱子,嘴上有两个倒钩,咬到人身上后,往出拔的时候就会带出来一块肉。这种小虫子有毒,被它咬了后轻则红肿,又痒又疼。个别严重的就是森林脑炎,得了森林脑炎,非死即废。听一起干活的人说,林场哪年都有人被草爬子咬后致死或致残的。
黑熊来时,我正在犹豫要不要多放一匙油安抚一下今天的疲劳。砰,我的身后一声巨响,我急忙回头,只见庞大、漆黑的一团在我眼前一晃而过,很快就消失在林子里了。母亲说,那是一头熊,被火光惊着了,奔跑的时候撞倒了一根枯树。
黑熊也吓到了我。第二天起我一直病怏怏的,睁不开眼睛,手上的活也打了折扣。咬牙,再咬牙,为了见校长,我当然能坚持。郑大叔说他跟校长很熟,他说他兴许能说动校长给我免了学杂费和住宿费。
相邻窝棚的李婶跟我妈小声嘀咕:“花儿还小,这要是吓出来毛病是一辈子的事儿,带她下山吧。”妈叹了口气,声音压得更低:“大老远的好容易折腾上来了,不挣俩钱儿回去哪行呀,花儿还想上学呢。”
接下来的几个晚上,妈一直给我叫魂。昏昏沉沉间,那声音忽高忽低、时断时续,仿佛来自史前,跋涉了五千年才微弱而执着地钻进我的耳朵。“花儿呀,不怕不怕呀——花儿呀,跟妈回家吧——哦,这里不是咱们的家。花儿呀,赶紧回窝棚吧——”妈,我不明明就在窝棚里么?
那个春天经常下雨,外面下大雨,窝棚里下小雨,到处都湿淋淋的,头发也难得干。一个星期以后,我的头上长了虱子。我从小就宝贝我的这头长发,我就要用留头发来表达我自己,不管侍候起来多麻烦。在家里没有面碱可用的时候,我就用滤草木灰的水洗头发,也挺滑溜。好吧,长头发剪了,我不能带着一头虱子进学校、见校长。李婶一剪子下去,我成了半大小子。
因为盼望着能见校长,我干活可仔细了,生怕出一丁点儿错会惹郑大叔不高兴。郑大叔这人不是一般的细致,下菌时添了个新家什,菌漏子,而且大漏子下面又安了一个小漏子做“嘴儿”,说这样不糟蹋菌。可我一用那漏子,菌就总会把那个“嘴儿”塞住,根本就漏不下去。而我们就是按照漏进去的菌数来计算钱的。小心了又小心,我对待木耳菌像对待稀世珍宝,我相信这一根根木耳段儿连起来是一条路,校长就在路的尽头。
越是紧张越是出岔头,我一着急,还被小锤子把二拇指肚儿上的肉整个儿砸了下来。钻心地疼啊,鲜血把一条手绢都染红了,还在流。郑大叔说:“你们大老远的出来,不就是为了挣钱吗?这不就是钱吗?怎么就不知道挣呢?手指头受点伤怕什么,不是还没折吗?”我坐在木耳段上,特别想哭,可我不敢,我怕错过了只有郑大叔认识的校长。
郑家的活总算干完了。放工钱的时候,我最后去的,半个月下来总算有了结果。妈妈数着手里的那些稀薄的毛票子,我却一直盯着郑大叔,他不看我。他是不是忙得忘了答应我的事儿了?我鼓足勇气走上前去,“大叔,你啥时候带我去见校长啊”,郑大叔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他说他和那个校长的关系其实也一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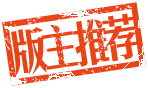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