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孙姜 于 2019-6-29 13:17 编辑
1
老张自然是被众人簇拥着坐在了首席,他冲一左一右哈了下腰,冲一屋子人拱了拱手。落座之后,小饭馆终于从刚才二十几个人涌进来时的冷飕飕与闹嘈嘈中回过神儿来,恢复了温和与秩序,店小二忙前忙后,菜一道一道地递送到桌上。坐在左边的大队长贾文武给他的杯里倒上了酒,右边的警务厅长岸谷亲自把筷子递到了他手里,老张知道这荣耀的分量,忙不迭地点头作揖。仰起头环视了一下,他发现一屋子的人都在拿眼睛瞅着他,似乎都等他说话。是该说点啥了,他觉得自己今天有这个资格。放下筷子,老张慢悠悠站了起来,左手端起酒杯,右手“咣咣”地拍了两下胸口:“马司令抬起腿刚要跑,我一个点射,一梭子子弹齐刷刷都给他点这儿了……”
一口酒灌进肚,老张开始回想下午的情形。三点多钟警佐找到他时,说发现抗联大头头,当时县城里没有像样兵力,大队人马都在各处讨伐。忙三火四地之间警佐还是纠集起19个人,除了正执勤的战士,就是像老张这样状态好些的伤员,老张推说闹肚子,在营房里呆了两天了。坐上一辆卡车他们急火火地扑向目标,到了山根儿也只是看到雪地里一排上山的大脚印,他们沿着脚印进山。往山里走了半个多小时左右,走在最前头的警尉补回头用夸张的动作和表情,无声地告诉身后的人山梁上有情况,全体人员迅速分成两队,一队从南边顶上去快速追击,一队向北在山半腰偷偷往前推进。扛着歪把子的老张一拱上坡顶就知道远处那个高大的人影就是马司令。
遇上了,这回是真遇上了!他的心扑通扑通直跳,说不清是欢喜还是惶恐。5年前他就跟着马司令一起在山林里摸爬滚打了,他太熟悉眼前这个人。马司令无疑比以前更瘦了,但却跑得飞快,两只手摆动到头顶上,大步跑去的样子活像一只鸵鸟在飞奔。他好像受了伤,左臂明显不灵便,无论他多努力双方的距离还是越来越近。随着又一梭子射过来的子弹,躲在树后的马司令厉声喝问:“谁是抗联投降的,滚出来我有话说!”
老张跟他的副射手白二、弹药手王三龟缩在一起,不敢吭声。早年当过胡子,老张跟白二、王三是五年前被抗联一师收编的,他们这拜过把子的铁三角两年前跟着师长贾文武一起从抗联逃了出来,投了日本人。实在是受不了山里那个罪,在老张眼里,谁给饭吃谁就是祖宗。过去日本人不敢在山林里过夜,抗联部队白天再难晚上还能喘口气儿,贾文武过来后就不一样了,那小子肚子里有几瓶墨水人也诡道,他太知道抗联是咋回事儿了,不仅把抗联的生命线给切断了——七十几个存放枪弹、粮食、布匹和药品的密营全部端掉——晚上还连续追踪,马司令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大伤元气。今天贾大队长在别处行动,如果他在追击肯定还会更顺利。老张躲在一个坑里不敢轻易露头,回头一撒眸,看到小张也伏在雪壳子里仄着耳朵缩着脖呢,他心里暗暗骂了一句:小狼崽子。
老张又啃了块炖鸡肉儿,一边洋洋得意地对岸谷汇报着:“对峙到下午4点来钟天都擦黑了,我们接到了您的命令开始向他射击,‘嗒嗒,嗒嗒——’,大家一齐向山那边缺口里的人影开枪,那个像大驼鸟似的身影一边翻滚着一边逃脱了。警佐让四五个人做监视哨留在山顶上观察人影的去向,带我们追了过去。这时跑得力气已尽的马司令还在用手枪乱射,双方距离是50米。我们开始喊话:‘我们知道你已经断粮好几天了,身上还有伤,怎么抵抗也没有用,痛快投降吧!’回答我们的还是一串串噼哩啪啦的子弹。等我们把包围圈推进到只剩30米时,俺老张手里的机关枪就说话了。嘿嘿。”他干笑了两声,可一桌上的人都大眼瞪小眼没啥反应,老张不高兴了。“他妈的店小二你过来,这什么鸡巴小鸡儿,没炖烂你就敢往上端,是不是不想活了?”老张“啪”地一摔筷子,把身旁心事重重的贾文武吓得一哆嗦。
2
还没等贾文武回过神儿来,从另一桌突然虎虎地杵过来一个人,是那个小狼崽子。这个年轻人此刻怒气冲冲,仿佛全世界的不平都聚集在他脸上了,他直眉竖眼地把酒杯往老张面前狠狠地一蹾,骂了句:“老王八蛋,你不得好死!”
郁郁寡欢的小张一直显得跟庆功宴的热烈和喜庆不和谐。他坐在屋子的一角,一会儿站起来烦燥地走动几下,一会儿又坐下唉声叹气。小张当初是马司令的警卫排长,二十天前携带机密文件、四条枪和九千多块抗联经费下山投降的。在宿营地从来都是小张一人与马司令同住,照顾其起居,传达他的指令,他本来是这个世界上最贴近马司令的人,自然也掌握着司令的行踪、活动特点和突围计划。马司令被紧紧咬住到最后被击毙,按理他才是功臣,最大的功臣。可今天这句斥骂,显然不光是因为嫉妒。
一时间屋子里沉默了,岸谷也只是瞅了瞅眼前这个年轻人,想说点什么终于又闭上了嘴——今天的气氛太微妙了,他不想引爆空气中的飘拂着的那些隐形炸药。
小张15岁遇到马司令前觉得自己活得都不如街头的狗,他甚至真的跟一条狗抢吃过一户人家的热乎猪食。父亲被抓了壮丁不知死活,母亲被鬼子凌辱后自尽了,他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孤魂野鬼。进了抗联的少年营他才活成个人。因为心思细密、少言寡语,他得到了司令更多的信任和关爱,马司令一有空就手把手教他读书写字,唱歌吹琴。小张虽然没说出来,可在心里马司令就是自己的父亲,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小张一直带着马司令送他的口琴,这把口琴在冰天雪地里,在丛林旷野间,曾带给他多少快乐?
小张是最后一个走近马司令那庞大的躯体的,当时在场的日本人说啥也不敢相信死者就是大名鼎鼎的马司令,尽管老张一再拍胸脯。一到跟前小张就受不了了,蹲在他脚边嚎啕大哭:“司令,司令你可不能怪我呀!我是害怕,我害怕,那些个零下40度的后半夜,大树都冻得嘎吧嘎吧直响啊,树干都冻裂了缝,人能咋办呢,抗联咋办呀……自从密营被那个王八犊子给破坏了,咱就没了吃、没有穿、没了存身地方,只能在野外露宿。入冬以来天天被小鬼子追着跑,司令,我宁愿跟你一直跑着,鞋子跑烂了、衣服刮坏了咱不是都用藤条和绳子什么的绑上了么?我怕停下来,停下来冷风一吹就像掉进冰窟窿里了……你领着我们蹦高,领着我们数星星,不管多冷咱也不敢生火,不管多困你也不让我们睡觉,你说睡着了可能就再也醒不过来了……司令,这回是你睡着了,真的就再也醒不过来了么?司令,你个话呀……”
小张的这些话显然冒犯了许多人,但谁也没跟这个沉没在悲情里的孩子计较。小张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仿佛要把这些日子内心的不安和愧疚全都倒出来,仿佛他的司令还听得到。等到他擦干眼泪,想再去替司令拾掇一下零乱的衣裤时,手伸到半空他又缩了回来,他明白,二十天前从司令身边跑开时自己就把这个资格弄丢了。
就像下午的哭诉勾出了另外几个从抗联反水过来人的眼泪一样,那晚小张的失态也传染了整个贾文武挺进队,庆功宴不欢而散。
3
是的,老张立了功,可立了功的老张不自在。 老百姓的憎恨是想得到的,那晚上饭馆里旁边一桌的两个戴眼镜的人听完了他的话,说了句“这饭吃不下去了”匆忙算账摔门走了,打那时他就知道亲手击毙马司令这件事儿不能再可哪儿嚷嚷了。他从不一个人出门,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张平生第一次感到恐惧。让他上火的是自从那天在酒桌上冷场以后,在讨伐队里也不咋有人搭理他。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头椽子先烂,老张懂得这个道理,他再不敢炫耀反而开始藏掖,再有人见面时说些什么“佩服”、“祝贺”之类的话时,他就说“瞎猫碰上死耗子了”,“托兄弟的福”之类的话儿,再陪上笑脸和点头作揖。
可怎么藏得住呢?评功授勋时上面给老张评了个与贾文武一般高的“勋五位景云章”, 这可是日本人给中国人的最高奖赏啊,铮明瓦亮的银质奖章加上个彩色珐琅的坠儿。老张说啥也不要,老张再贪也没贪到不要命的地步,他不傻,他已经意识到接下来的日子能平平安安地混下去就行了。可要不要由不得他,给脸不要脸更不是好事儿。等他领了勋章后,队里的弟兄当面儿就挤兑他:
就你有能耐啊,给日本人办事儿最卖力气 你是真风光了,弄得哥几个没法混了 你老张是狠茬子,以后可得离你远点儿了,别哪句话说不对了被“点”了 等着吧,日本人的庙里还能给你立活牌位呢
神枪手老张现如今越来越怕,像只吓破了胆的豹子,深深的恐惧折磨得他寝食难安,度日如年。
小张下山的目的只是想吃得饱、穿得暖,但代价是必须告诉日本人马司令的行踪和突围路线,他也不想说,可不说不行。小张本来很满意现在的状态,庆功宴闹了那么一出后他很快就后悔了,在内心深处他惧怕那个老张,那老小子的狠劲儿他早就知道,胡子头出身哪,神枪手呀,弄死个人还不跟踩死个蚂蚁似的?小张从来不敢直视那对深陷下去的眼窝,觉得那里飕飕地往外冒凉气。以后还得在一个槽子里打食儿,得想办法往回拉拉味儿。
这天,小张找了贾文武:“哥,我是冲着你才下山的。我岁数小,那天在酒桌上不该那么跟老张说话,你帮我圆一下吧。”贾文武下意识地收了收越来越鼓的肚子,扶了扶眼镜,说道:“小狼崽子,老马肯定上辈子欠了你什么,这辈子活活栽在你手里。唉,行吧,老张那里我也正有话要说,晚上一起去酒馆吧,一会儿没人时你知会他一声。”
一端起酒盅,老张就急忙抢着说话:“大队长,我正想找你呢,我这个功立得日子不好过呀,黑天白天连个囫囵觉也不敢睡,现在瞅谁都像抗联,个个都想找我索命。”
贾文武“吱”地干了一盅,左瞅一眼右瞅一眼:“咱们这些从山上下来的哪个不是这副德性?个个心里都打小鼓,谁的日子也不好过,走上了这条道,也只能是活一天算一天了。这满洲国的龙椅也不知道能不能坐长远呢,有可能现在露多大脸将来就现多大眼,依我看哪以后咱们都夹起尾巴的好。”吃了两颗花生豆,看到小张眼巴巴地盯着自己,他转向老张:“小张那天在酒桌上冲撞了你,你得大人大量,他虽然是老马一斗米喂出的仇人,可也毕竟是在他身边长大的孩子,有感情。”小张也急忙站起来冲老张点头哈腰,双手把酒杯举过头顶。
“一笔写不出两个张字,贾队长你就放心吧。”老张的心思不在小张上,这小狼崽子成不了气候,他心里有数。急忙咽下小张敬的这盅酒,他又把脸儿转向贾文武:“大队长你得替我想想招儿,成天到晚提心吊胆的,我快撑不住了。”
贾文武瞅瞅老张,又瞅瞅小张:“我呢当了这个大队长,想不显山露水也不可能了,只能硬着头皮往下混。你们俩呀,我看可以从此改名换姓,回头我把你们调到没人认识的小队去,剩下的事儿,你们好自为之吧。另外,从现在开始你们得对外散布假消息,就说老马是自杀的。”
“自杀,能有人信么?”老张小张异口同声。
“编匀乎点儿,时间长了大伙就信了。你们就说马司令枪里只剩最后一颗子弹,高喊了一声‘宁死不吃满洲国的饭’,然后开枪身亡。”
4
五年以后,日本战败,岸古用氢化钾毒死全家人后剖腹自杀。一直跟在他左右的爪牙贾文武在枪杀了几个投降的日本俘虏后,居然成功地混入华北野战部队,还当上了指挥员。
1951年夏季的一天,沈阳城里下起了大雨。贾文武在街上走着,一个也穿着军服的人为避雨钻到他的黑布伞下,一对眼儿,两人都愣住了。
“大队长,是你呀。” “你怎么也在这里?老张他们三个被毙了,你知道吧?”贾文武收回目光,忧郁地看着远处。远处,庆祝沈阳第三橡胶厂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条航空轮胎的秧歌队被突然到来的大雨浇散,热烈的喧闹声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 “知道。六年前,在司令坟前。” “死了好呀。” “可不是嘛,天天晚上都是做不完的噩梦,还是死了痛快。”
第二天,这两人同时出现在公安局门口时似乎都没为这又一次的不期而遇吃惊,只平淡地对视了一眼。 “我有罪,我来自首。他,也是坏人。”两人互相指着对方,异口同声。 不久,贾文武和小张在肃反运动中被一起公审处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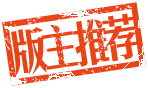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