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枫叶飘飘 于 2017-4-11 08:04 编辑
芒刺
陆颖胡乱洗了个澡,用毛巾包裹住湿漉漉的头发,就迫不及待地换上了新买的那套鹅黄色内衣。 那套内衣价格不菲,她狠狠心用一件羊绒大衣的价格把它买了回来,陆颖早已无计可施,这是她最后的武器。
陆颖一只手拽住乳罩的底边,另一只手做虚握状伸进了罩杯,那只拽住底边的手向下拉住,伸进罩杯的手环包住乳房用力向上拔了一拔,刚才还虚软的乳房立即坚挺起来,如是的动作又在另一只乳房做了一次,一条深深的乳沟便嵌在了两个乳峰之间。 接着她伸手拉了一下吊在胯下的三角短裤,这短裤短的让人不可思议,几乎刚刚够遮住陆颖的私处,大腿根两边仅一指宽的布条延伸到臀部,而透过肚脐下的镂空花边,陆颖居然看到丛丛黑晕若隐若现,她禁不住又把短裤向上拉扯了一下。像一个即将登台的演员正在舞台的暗处候场,陆颖从心理到生理都做好了随时登台的准备。
临近午夜,陆颖的心开始砰砰急跳起来,她感到自己有点缺氧,随手在冰箱里拿了一瓶饮料一饮而尽,即刻打了个寒颤,她把空调的温度稍微调高了一些,慢慢平复了一下情绪。
丈夫杜凯就要回来了,最近半年的时间里,陆颖已经摸透了他的作息,不到她睡去多时不可能回家,理由永远只有一个:学校事多人少。 陆颖小手指轻轻一勾挑开了真丝睡衣的腰带,露出里面鹅黄色的内衣,然后她关掉了吊顶大灯,再打开走廊和几个角落的夜灯,灯光柔和而迷离。陆颖此时也有点春心荡漾起来。
这是一个三室一厅的套房,一主卧一次卧,还有一个是给未来孩子准备的房间。然结婚两年以来,陆颖几乎没有尝过翻云覆雨的销魂,更没有过颠鸾倒凤的交欢,或许是延续了陆颖追求杜凯时的心理角色,陆颖在这方面总要偷窥杜凯的脸色,她不敢多要求什么,刚开始她甚至以为夫妻生活本就如此例行公事。 与往日不同,陆颖没有去主卧而是蹑手蹑脚直接进了次卧,这个平日里为客人或者父母留宿准备的房间,杜凯时常回来过晚便悄无声响地在次卧睡上一宿,第二天早上再解释说怕打扰陆颖休息。这样不能令人信服的借口一再反复,倒呈现了一个让陆颖觉得十分可笑的局面,主卧归陆颖,而次卧的主人是杜凯,这与分居又有什么实质的不同?陆颖早就耿耿于怀,却没有勇气质问,她不能想象质问后的结局,她不能失去杜凯。 陆颖贼一般潜入次卧以后,躺在床上怎么想都觉得自己既可笑又可悲,这不自己的家吗?如今她怎么倒像是一个被人所不齿的偷情者潜入了别人的卧房呢?
门外有钥匙开门的响动,虽声音轻微但还是让陆颖即刻警觉起来,是杜凯。陆颖下意识地一把扯过夏被蒙住脑袋,像是光天化日之下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片刻的沉寂,陆颖轻轻把夏被拉至颈部,只露出自己的脑袋,像紧裹着一条睡袋,她屏住呼吸听着门口的动静。
杜凯进了屋,又转身小心地轻轻合上门,换鞋的声音,放包的声音,挂外套的声音。陆颖的眼睛跟着这些动静打转,嗓子干涩难耐,她尽可能地压抑着。
等杜凯站在了次卧的门口,陆颖已是闭眼做熟睡状,夏被已褪至胸部,半遮半掩,一头半干半湿的秀发铺散在枕头上,散发出阵阵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
时间仿佛凝固,次卧的门口没有任何声响,既没有远去,也没有走近,就这么停滞在了那里。
陆颖忍不住微微睁开了眼睛,次卧的门口,走廊夜灯迷蒙的灯影里站着一个黑影,正是杜凯。
“你回来了啊?”陆颖半欠起身,一只手撑着床,一只手揉搓着眼睛,半卷的长发倾斜到身体的一侧,隐隐地遮住半边呼之欲出的乳房。
“嗯,回来了,学校太忙,累的精疲力尽。”
没等陆颖体恤,杜凯极力掩饰住诧异的表情接着问:“怎么睡这边了?这么晚还没睡?”
“我特意过来等你的啊。”陆颖做半羞状,一对浅浅的酒窝在脸上漾开笑容,妩媚迷人。
“等我?有事吗”杜凯显出些许惊讶地走到床边坐下,陆颖顺势将身体靠了过去:“没事啊,妻子等她的丈夫还需要什么理由吗?”陆颖边说边娇滴滴地将一双玉手环搂住杜凯的颈项。
“别闹别闹,我今天真累得够呛,腿都直打飘呢。”杜凯小心地轻轻推离着陆颖。 这一推非但没起作用,反而让陆颖一下子直立起身体,半跪在床上把杜凯搂得更紧了,任杜凯怎么左右扭动都无法挣脱,他不自觉地站起身来,跨离床边一步。
陆颖紧跟着赤脚跳下床来,又一把环抱住杜凯的腰际,像一头母豹一下子狠狠地擒住她的猎物。睡衣轻柔地滑落在地,露出陆颖那套性感的鹅黄色内衣。
陆颖结实的小腹紧紧贴住杜凯的屁股,坚挺的胸部也随之用力紧贴着杜凯的后背,热唇柔滑如丝般吻着杜凯的后颈,双手在杜凯的身上来回摩挲着,揉搓着。陆颖蛇一般控制不住地扭动着身体,身上的每一寸肌肤都紧紧贴着杜凯,她闭上了眼睛,喉间发出梦呓般的呻吟。 杜凯对陆颖这反常的疯狂举动吓得不知所措,他下意识地左右躲闪保护着自己,像是一个被恶意侵犯的少妇,那只被陆颖强拉进三角短裤的手甚至不自觉地握成了拳状。
陆颖显然没有善罢甘休,她强拉硬扯地把杜凯往床边拽着,杜凯一个趔趄重重地压在陆颖的身上。
“够了!”杜凯忍无可忍,全然不顾夜深人静控制不住地大喊一声,陆颖一下子瘫软在床。
杜凯从陆颖身上爬起来,转身就要离开。
“你要去哪儿?”陆颖大声喝住杜凯。
“去睡觉!你是在这儿睡还是去你房间?”
“什么叫去我房间?这是你房间?我们分居了吗?”陆颖尴尬而心痛,那套昂贵的内衣没能让杜凯缴械。
杜凯没有回答陆颖,继续转身走出次卧。
陆颖再次赤脚跳下了床,紧跟着杜凯奔向主卧。
“你到底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躲着我?我有什么不对的你可以说出来,你这算什么?”
“你很好,你没什么错,错都在我!”杜凯似是而非地回应。
“错都在你?什么错?你有什么错是我不知道的?”
“没什么。”杜凯浑身无力,他感觉自己异常疲惫。
“没什么?不对!你肯定有什么!”陆颖斩钉截铁,她从未有过的笃定。“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陆颖的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
“没有!”
“没有?干嘛还不敢承认?男人做事要敢做敢当,你还是个男人吗?我看你就不配做个男人!”
“是!我不配行了吧?”这句话彻底激怒了杜凯,他唰地起身又要转回自己房间。
“不许走!”陆颖开始声嘶力竭,她摇晃着脑袋用尽了全身力气大喊,披肩的长发扑散在她的脸上看不清眉眼。陆颖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杜凯呆立在主卧门口,背对着陆颖,久久没有挪步。
此时陆颖完全处于失控状态,她开始滔滔不绝诉说她这些年的感情压抑,所遭受到的冷漠和孤独。委屈和埋怨如山洪暴发般沙石俱下,那鹅黄色性感的内衣也早已失去了光彩,一条肩带滑落在臂膀,显得滑稽可笑。
杜凯倚在门框上静静听着,没有反驳一句也没有安慰一句,等陆颖筋疲力尽语气越来越轻近乎于自言自语时,杜凯转过身来,非常凝重地看着陆颖说了一句:“颖儿,我们离婚吧。”
陆颖正耷拉着脑袋调整着气息,没成想一下子被人从火山踹下了冰窟,这个人正是自己的爱人杜凯。陆颖使出全力抬起头睁大着眼睛瞪着杜凯:“你刚才说的什么?你再说一遍!”
“我们离婚吧!”
“这是你说的?是你说的吗?你可别后悔!”
陆颖咚咚咚地打开厨门翻找衣服,把满厨花花绿绿的衣服扔个满地。
“你要干什么?”
“我走!离开你这个无情的冷血动物!”陆颖嘶叫着。
“别别!我走,你留下。”杜凯无力地说。
“那你快滚啊!快给我滚啊!”陆颖揪扯着手里的衣服大叫着,仿佛再多等一刻陆颖就会扑上去撕开杜凯的胸膛,扯出他的心脏,看看那滴落的液体究竟是什么颜色。
杜凯走了,影子一样消失在了夜幕里。陆颖空了,剩下一个冰冷的躯壳,躯壳上套着那套滑稽的鹅黄色内衣,她被杜凯“杀了”。
杜凯走的十分决绝,这在陆颖是绝没有预料到的,她觉得他们的关系绝不至于走到离婚的地步,她也曾怀疑过杜凯对她有所不忠,她甚至为这个猜疑设想过无数个原谅他的理由,然而杜凯却决意直奔离婚,没有丝毫回旋余地,并且是他毫无条件地净身出户。
一年以后,陆颖仍像在噩梦中无法醒来,像眼下这正值隆冬的季节,陆颖希望自己的心和灵魂都被冻结起来,永世封存,哪怕被撕开一丝缝隙,都会让陆颖皮开肉绽如受炼狱般煎熬。她想不通自己错在哪里,早在哪一步就决定了自己如此不堪的归宿?
“叮咚!”门铃的声响,陆颖死气沉沉地起床开门,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站在门口,陆颖警惕地看着对方。
男人确定了陆颖的身份,交给她一封白皮信封,匆匆消失在夜幕之中。
关上房门,陆颖带着满心疑惑回到卧房,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陆颖的心随即一紧,杜凯,是杜凯的字。陆颖的心砰砰急速跳动,她快速按开了吊灯,屋内即刻通明起来。
颖儿:
你还好吗?是我,杜凯。
颖儿,请允许我最后一次这么叫你,并送上我深深的歉意,我知道你不会接受,但我仍然要让你知道,在这个世界,我最对不起两个女人,一个是我的妈妈,还有一个人就是颖儿你了。
颖儿,你是一个好姑娘,好妻子,一个优雅贤德的女人,我妈妈常跟我说:颖儿是个多好的姑娘啊,找到她可是我们家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啊!
可我没这个福气,我是一个“凶手”,一个同性恋者。
颖儿,当我确信自己的性取向与常人不同时已是接近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疯狂地爱上了我,尽管你很优秀善良,我喜欢你,但我并不爱你,真的不爱你。
可我想到了妈妈,我那个守寡多年独自把我培养成人的妈妈。我没脸让她知道我的“变态”,她一直盼望着我能早点结婚生子,找一个贤惠善良的妻子,这是她一辈子最大的心愿。 这几年,我一直刻意逃避着结婚这个话题。可是颖儿,妈妈越来越老了,没太多的时间等下去了,她腰椎不好早早地就佝偻了脊背,一只耳朵也早已失聪,我唤她的时候要特意绕到她的右边,她歪着头仔细地听我说话才知道我说了些什么。
颖儿,我好悔!悔的是我坑害了一个如此善良纯真的姑娘,我选择了你做我的新娘,我原本以为娶了你我会因此而改变,或许我之前没有感受过女人的魅力而导致我性取向的扭曲?
还有一个罪恶的念头,我想用你来安抚我的妈妈,哪怕只有几年,我也想让妈妈拥有这最后的快乐,这是多少金钱都换不来的。你做到了,这两年妈妈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幸福,她是那样地欢喜你这个儿媳,她为你做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唯一能为你做的,就是不停给你做这样那样好吃的,只要你说哪样东西是你爱吃的,妈妈佝偻着她的脊背,用那几乎失聪的耳朵到处打听也要给你买些回来,然后用心地做好端到你的手中。
颖儿,近半年我压力好大,一方面是妈妈急切的盼望在她离世前能抱上她的孙子,另一方面就是你。结婚以后,我越来越确信自己的“同志”身份,也越来越醒悟到对你犯下的这个不可饶恕的罪恶,我把你做了我性取向的殉葬品。
你知道,在中国,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在超过适婚年龄而迟迟没有动静是件压力多么巨大的事情,亲友、同事、同学、朋友,他们喋喋不休的“关心”着你、猜疑着你,足以将你的生活摧垮。我怕了,我和你终于组成了一个貌似“正常”的家庭。
然而这一切都是以牺牲你的幸福作为代价的,我无时无刻不在告诉自己要尽早放你自由,也无时无刻不在忏悔自己的罪恶,终于有那么一天,当你穿着那套鹅黄色的内衣向我扑来的时候,我彻底痛下了决心:该结束了!
颖儿,跟你离婚以后,我原本以为我终于可以追求我自己的幸福了,虽然它是被常人所不齿的,但我已经结过婚了,结了婚再离婚那是因为感情不和,我摆脱了人们用异样的眼光告诉你你是不正常的,这是以你为我的牺牲换来的,所以我用净身出户作为你的补偿,房子和财产都归在了你的名下。
离婚以后,我去找了之前喜欢过我的一个律师,他一直在等我离婚,我想,如果慢慢地让妈妈也能接受他,我们一样可以让妈妈的晚年过得幸福。但我错了,他没等到我离婚就找了一个没有过婚姻的年轻伴侣,他嫌弃我是结过婚的,说我是不仁不义的人,既然知道自己身为“同志”还要坑害别人,为求得自己心安而置他人于死地。
颖儿,我没脸再活在这个世上了,我是一个被世界抛弃的人,唯一还抛舍不下的就是我那年迈的妈妈。我已经用我之前晚上做家教的积蓄和妈妈的房子做为抵押签定了一个合同,给妈妈找了一个好一点的养老院,我想那将是妈妈最后的归宿了。
颖儿,我知道对于你我是个罪人,但看在妈妈往日疼爱你的份上偶尔去看看妈妈好吗?告诉她我调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工作,要很久很久以后才能回家来看她。 至于我颖儿,我还在寻找我的归宿,是一座无人问津的高山?还是一条古老深远的河流?亦或是一棵初长成材的小树?
不要找我,有急事去找送信的那位大哥,我会留下他的联络方式,他也是一名高校老师,我们有着相同的境遇,他会尽力帮助你的。
最后,一万个对不起!
颖儿!答应我,未来一定要让自己幸福,一定要睁大你的眼睛,把自己托付给一个真正爱你的人。
罪人杜凯 于二零一四年隆冬的一个深夜 看完信,陆颖早已是泪流满面浑身颤栗,她的心一阵阵绞痛难忍,一阵阵怒火中烧,她感到吊灯在旋转,整个屋顶在旋转,甚至整个世界都在快速旋转。她赶紧慢慢躺下闭上眼睛,调整着自己的呼吸,而脑海里还刻满着杜凯信中的字迹,如幻灯片一样快速闪烁,无力自拔。
之后的两个多月里,陆颖反反复复咀嚼着那封信的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她无数次撕扯着自己的伤口,让它们流脓、流血然后结上硬硬的疤结。陆颖的心慢慢开始平复,有块柔软的东西在心口里轻轻涌动,她恨杜凯,恨不得立刻杀了他,但她也明白,自己曾强烈地爱过杜凯。
在一个雪花漫舞的夜晚,站在窗前的陆颖想起了杜凯养老院里的妈妈。
快过年的时候,陆颖把杜凯妈妈接回了自己家里,再没有送回那个养老院。
冬去春来,四月的南京已是枯木逢春、桃红柳绿的季节,每年的这个时节,人们都从四面八方涌向著名的鸡鸣寺去观赏花团锦簇的樱花,陆颖小心搀扶着杜凯妈妈,缓慢地走在喜悦的人流中......
后来据那位送信的大哥说,经他苦口婆心地开解和劝导,杜凯最终去了一个异常偏远贫困的山区支教,或许会永远留在那里。
用不了多久,杜凯就会回来接他的妈妈了,陆颖心里这么想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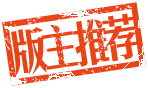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