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逐鹿江南 于 2017-3-27 12:16 编辑
拴住是我的同族伯父。人们几十年来一直这么叫,他的真实名字始终无人提及,恐怕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了。
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乡长,后来去了台湾。因为这个缘故,他的母亲被定为“四类分子”。自然,他的境遇也随了母亲沉沉浮浮。
在那个疯狂的特殊年代,成分不好是颇受人歧视的,甚至要付出难以想象的惨痛代价。
听父辈讲,在拴住伯的母亲被贫下中农抓去批斗时,村里的小孩子们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到他家将年仅四、五岁的他揪出来,在他脖子上挂一块硬纸板做成的写有“反革命分子”字样的牌子,押着他满村“游街”。他睁着一双惊惶的眼睛,不明白批斗的真实含义,只是一个劲地张着小嘴大哭。一班大大小小的孩子跟在他身后,群情激奋地高声呼喊口号,将紧握的拳头举得老高。当他的母亲喝散众孩子,将他解救出来时,他的衣服被撕扯得支离破碎,脚上的鞋也不知去向,身上的肌肉青一块紫一块。
作为护犊的本能,母亲用一条绳子将他拴在家里,绝不让他出门与别的孩子玩耍,以免受到伤害。母亲出工的时候,无一例外地将他带到地里,拴在旁边的树上或大石头上。
久而久之,拴住这个称谓就传开了。他的真名渐渐被人们遗忘了,他的母亲也随了大家这么呼叫。
因为时时被拴,拴住伯习以为常,并且形成了严重的依赖性。倘若一天不被拴,他就会吵闹着要母亲将他绑起来。除了走路以外,吃饭的时候需要拴,上茅房的时候需要拴,就连睡觉的时候也需要拴。总之,一天不拴,他就一天难受,心里觉得这日子不踏实,没法过下去。这就像喜欢吃辣椒的人一样,明知辣得难受,却偏偏离不开。待到辣得满头大汗,还一边哈气一边大喊:爽!这大概就是心理学家反复论证的所谓受虐狂理论罢。
人实在是最坚强的动物,无论怎样艰难的环境,都不能阻止他的生长。这正如一块无论多大的石头,都不能阻挡一棵孱弱的小草从它重压下的缝隙间生长出来一样。
拴住伯在母亲绳索的护佑下,一天天成长。
到了上学的年龄,拴住伯哭喊着死活不去学校,理由是教室里没有地方可拴。他的母亲搂着他抹了半天眼泪,终于在老师的帮助下想到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将绳子的一头拴在他的腰间,另一头系在教室的屋梁上。
拴住伯惴惴不安的情绪才算平复下来,安心地坐在教室里上课了。
老师叹着气,说,造孽啊,这孩子!只听说过古人头悬梁,还从未见过腰悬梁的,真是千古奇观!
小学毕业了,拴住伯做了农民,随着村民们下地挣工分。在广袤的田野里,要将人拴起来,且不影响劳作,着实让母亲伤透了脑筋。好在人是最有智慧的高级动物,无论什么样的困难,总有应对之策。
出工的人们惊诧地发现,田里竖了一截木桩。一条绳子,从木桩延伸到拴住伯的腰上。拴住伯挥动农具,与村民们一样迅捷地劳作。当劳动行进到绳子的极限长度时,母亲就拔起木桩,钉到目标前面,如此反复移动。大家啧啧称奇,叹为观止。
就这样,一条绳子,总是拴系着拴住伯的腰,也拴系着他的冷暖人生。
后来,拴住伯结婚了,生儿育女了,土地承包了,他的人生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唯一没有改变的,是那条永远拴系在他腰间的绳子。
再后来,母亲走了。拴住伯将自己拴在母亲坟前的苦楝树上,长跪不起,大放悲声,痛哭了三天三夜。他怀念那个给了自己生命,并且穷尽心思,用绳子呵护了自己一生的女人。
如今,已经七十多岁高龄的拴住伯,身体已大不如前,极少见他露面。我前几天看见他坐在墙根下晒太阳,一脸沧桑,两眼茫然,俨然患了痴呆症一般。问起他的过往,他摇着头说想不起来了,也不愿去想。他能清晰地记起的,就是自己被拴起来的一幕幕场景,以及那些陪伴他度过了大半生的各种各样的绳子——麻绳,草绳,竹绳,棕绳,尼龙绳……。
望着拴在牛栏柱子上的拴住伯,我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之中。我困惑不已,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发问,一条没有立场的绳子,究竟与生命之间有何必然的关联?是不是也如这牛栏里的牛一样,当一条绳子系在它的身上,它的生命就为我们人类所保护和掌控?
2017年3月18日,无锡
宿命的绳子
——兼谈《拴住》的创作
如果我说绳子是人类最早使用的工具之一,大抵是没有多大争议的。可以想象,远古的人们,利用绳子结网捕鱼,猎杀动物,用绳子将木头捆绑起来,搭建居住的房屋。仓颉造字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学会了结绳记事,翻开了文明进步新的一页。可以说,一条条普普通通的绳子,将人类文明从蒙昧的洪荒时代一步步推向前进。
绳子很多时候也是正义的象征。君不见那些作奸犯科的歹人,一个个在绳索的威力下耷拉着一向狂妄的脑袋。打开历史的画卷,我们可以看见一条条绳子,以其牢固与韧性,维护着社会的基本道德与法制,促进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我们不难想象,在一个缺乏绳子约束的社会,与非洲大草原上狼奔豕突的禽兽世界有何区别。绳子,在这里就是秩序。
然而,绳子本身是没有立场的。这就决定了它难免会产生一些问题,甚至是巨大的问题,有时大得比它的正面效应还要大。
在将丑恶“绳之以法”的同时,绳子也制造冤假错案,自古以降,一幕幕永不停歇地上演。这方面的例子俯拾即是,无需一一枚举。
最可怕的,当是无形的绳子。它将我们捆绑,却又让我们无所觉察,甚至习惯成自然,让我们安于“戴着镣铐跳舞”。
听父辈讲,我们家邻居中曾经有一位私塾先生,当时已经七十几岁高龄了。他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堂屋里设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下,毕恭毕敬地三鞠躬。在自家如此,到别人家的堂屋亦是如此。甚至只要有人说到“孔子”的名字,他都会站起来鞠上一躬。
“文革”时,这位老先生被作为“牛鬼蛇神”批斗。当红卫兵骂他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时,对方刚说出“孔老二”几个字,他已经深深地鞠躬了。红卫兵问他为什么对孔老二的名字那么敏感时,他回答,他的先生教的。如若鞠躬晚了,就要挨上先生戒尺的严厉责罚。为此,他受到的惩罚数不胜数。在先生的反复教育下,他习惯成自然,对那个名字产生了条件反射。
听了父亲讲述的这个近乎于段子的故事,我没有如众人一般大笑,心里沉沉的很不是滋味。我想,这位传统教育濡染出来的先生,是被一条无形的绳索绑架了一生。
太可怕了!只要想起这个故事,我就会惊出一身冷汗。
学生时代,我对历史是极有兴致的,对教科书中一些英雄人物事迹的叙述,常常令我热泪盈眶。及至中年,读的书多了,杂了,以及阅历的增长,才明白事实远非那么回事。我们常说“自古以来我们怎样怎样”,其实,这个古究竟有多古?自古以来真是这样么?“大一统”的历史观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是我们这个民族不自信的表现。不自信也就罢了,可是却通过教育,将一条无形的绳子,套在孩子身上,让他们分不清真假,辨不出是非。
经常听人说我们的孩子在学校学习成绩极好,可是创新能力却远不及西方的孩子。前些年对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大师的讨论,就是明证。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一定是教育。我们将一条条自以为是的绳子,绑在孩子们身上,牵着他们在所谓的“正道”上行走。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固然有许多足以让我们自豪的东西。然而,如果过于迷信盲从而因循守旧,则是把一条无形的绳子套在我们身上了。
可叹的是,在我们身上,还能依稀看见一条条无形的绳子,将我们牢牢地捆绑着,让我们施展不开手脚。更可悲的是,我们习惯了这样的绳子捆绑在我们身上,根本感觉不出它的存在,即便感觉出来了,我们也没有解除它的勇气,甚至认为没有解除的必要——中华民族特色的绳子解除了,我们还是中华民族吗?
绳索是我们民族的宿命。它在助力中华文明的同时,也束缚了我们的行动。要解除它,绝非一日之功。
在你身上,有没有一条这样的绳子? 2017年3月26日,无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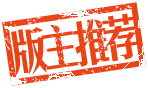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